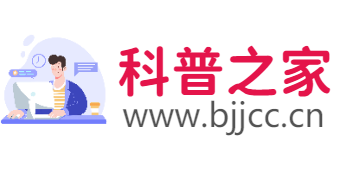汤楠:因新冠而受损的肺能复原吗?|女科学家去哪儿了
时间:2022-07-05 04:20:59 来源:科普之家 作者:返朴 栏目:前沿 阅读:52
“我真心认为,只要是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肺,感染新冠之后都是会恢复的。”
——汤楠
受访 | 汤楠(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采访 | 韩若冰
在肺研究领域,“肺再生”曾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不可能之事。这里说的再生,指的是肺脏损伤后的修复,包括肺泡(肺脏用来交换气体的单位)结构的重建和纤维化的消退。
去年疫情初期,国内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预后情况牵动人心,不少轻症患者也对自身肺部的康复前景忧心忡忡。
直到2020年7月6日,《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 杂志在线发表了一篇关于新冠肺炎患者肺泡再生的文章[1],研究通过分析两名成年COVID-19患者的肺组织,观察到在病毒性肺炎感染后期,肺泡干细胞(AT2)能够增殖并分化为负责气体交换的肺泡I型样上皮细胞(AT1),表明急性损伤后的成年肺仍然拥有一定的修复能力。
带领这项研究的专家,正是今天文章的主角——汤楠博士。
如今,越来越多的临床证据显示,一部分早期幸存者的肺正在慢慢自我修复。与此同时,如何促进肺的恢复和再生的研究也变得更加火热。汤楠认为,这确实是基础研究应当集中力量做的事情。
人物简介
汤楠博士于2012年加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自2019年至今任该所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肺再生机制,以及重症、难治性肺病的病理及治疗。1993年,汤楠获西安交通大学医学学士学位,2005年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分子病理学系获博士学位,2006-2012年期间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解剖发育生物学系进行博士后研究。
图片授权:汤楠
“我自己都忘了,当年的理想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实验室”
1993年医学本科毕业之后,汤楠进入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为一名临床医生。几年后,为了实现自己的研究理想,她放弃了这份稳定的工作,赴美继续求学。在完成博士学位之际,她也没有听从导师的建议,选择经费更充足的乳腺发育研究,而是凭借一腔热情进入了“冷门”的肺研究领域。回顾这些人生中的关键节点时,汤楠说,对她而言,做出这些决定并没有特别困难。
返朴:医生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已经是非常好的职业,您为什么又选择去国外求学?
汤楠:90年代末的时候我在国内读研究生,当时用的还是水浴锅的PCR,吱吱响还特别慢,我就特别渴望去发明这种技术的国家看看。美国那时候对我们来说还是传说里的,没有那么多信息接触的,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时既然有出国的机会,我也一直挺喜欢做科研,就直接去了,没有太多稳定方面的考虑。
而且即便是在90年代末,好的医生也大都是做科研做得好的医生。医院已经很注重通过科研成果去评级,所以我觉得选择去做科研是顺其自然的,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想法。
返朴:您做医生的这段经历,对您以后做研究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汤楠:做医生的经历特别有用,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基于我对很多疾病的认识和了解,在去听研究报告的时候,有时候能够听出其中和临床脱节的问题。
第二点,我觉得是因为自己学过医,所以很注重生理和病理方面的问题,不过从研究项目的全局来看,这样可能既有好处也有坏处。毕竟,根据体内的分子生理工作,去找到蛋白互作(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和相应的生化机制还是很难的。
返朴:您在国外后来决定往肺研究方面转的时候,导师有不同意见吗?
汤楠:我在UCSD的博士生导师叫Randy Johnson,他属于比较“放手”的导师,不会给你特别多的人生建议。不过我说了我博后申请了UCSF(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Gail Martin实验室,Randy也会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想做气管分支发育,他说做乳腺研究也很好,经费更充足,“以后你就知道经费有多么的重要了”。但他也只是建议,并不会强烈反对我的选择——我们难道不就是因为兴趣才做科研吗?
返朴:您当时有考虑肺研究领域经费少的问题吗?
汤楠:我完全没有这个顾虑。第一可能真的是不懂,用现在的话说是“too young too simple”。第二,我想在博后期间做开创性的研究。
我本来是做血管发育的,在器官形成过程中,血管会伴随着主要组织结构发展,就比如主要组织搭了一座楼,血管就像布线一样布好了,它是有一定规律的,后来我了解到,肺的每一个大气管都会伴随着一根血管往前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模型,是我当时特别想做的事情。所以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相信我一定会有所成就的,还是有点莽夫状的感觉,傻乎乎地就去做了。
近来有次回家,母亲拿出了汤楠大学毕业时的同学录。汤楠回忆说:“我们那代人的同学录,封面要写上自己的名字,最好贴张照片,还要写上最大的理想是什么,我没想到我当时的理想就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实验室。我觉得特别amazing!我都忘了自己曾经的理想。”
虽说淡忘了同学录上的“豪言壮语”,汤楠的工作和成绩都彰显了她未忘初心。博后期间,汤楠专注于肺脏发育,探究受精卵如何一步步发育形成肺的器官,加之对成年肺的结构和细胞组成的了解和兴趣,她逐渐发现了内心最喜欢的东西,那就是:做肺再生和疾病相关的研究。从2012年回国加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来,汤楠不但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更是带领团队解决了领域内多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被预印本拒过,我的人生完美了!”
在汤楠还是一名医学生的时候,当时学界的共识是,肺一旦受损便不能再生。世界上第一篇报道成年人出现新的肺部生长的文章[2]发表至今还不足十年,可以说“肺再生”仍然是一个较新的概念。汤楠一直期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对这一领域产生兴趣,她喜欢与专科医生交流合作,也会带着问题和其他学科的专家沟通,学术上的拓荒不是茫茫黑夜漫游,而是互相照亮方向。
返朴:您所关注的肺再生还有肺的常见疾病领域,整体的科研进展处在哪一个阶段?
汤楠:都还是在非常基础的阶段。比如说我们2020年初发表的文章[3],才真正第一次了解肺纤维化到底是哪个细胞出问题了,又是怎么出问题的。
我在美国的时候,不少人认为肺病不是富人得的病,而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但其实随着人的寿命增加,肺病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衰老性疾病,大家都非常需要这方面的研究。比如特发性肺纤维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IPF),我们叫做不是癌症的癌症,病人通常发病就2、3年就去世了,也有很多名人死于IPF,所以肺病不能说就是“穷病”。
很多的肺疾病,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病(简称慢阻肺,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这种大病,在WHO全球死亡原因前十位里面,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科学家至今没有找到病因。
目前肺里发现的分子靶点主要是针对哮喘的,也研发出了一些相应的支气管舒缓剂。但像肺纤维化、COPD这几个大病的分子靶点不是特别多,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每次出去交流的时候,都非常欢迎研究者加入到肺领域,因为我们有太多未知的问题,很有希望发现新东西。
返朴:您有和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沟通合作的事例吗?
汤楠:我特别喜欢跟其他领域的专家合作,比如说我们实验室早期做力学有关的项目,和清华大学的杨春教授有合作,她是航空航天系专门做生物力学的。再比如我们遇到图像上解释不了的问题,会寻求清华大学的胡煜成博士的支持。目前的合作者还包括我们研究所的免疫学专家徐墨老师等等。
肺研究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狭窄的领域,其实我希望能有更多跨学科的互动交流,这样才能帮助你发现自己不了解的事情。
在新冠肺炎患者里面,许多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是重症炎症风暴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X光拍出来是“大白肺”,肺里充斥了无数的免疫细胞。然而这么重要的问题也难以解决,因为免疫学家虽然了解血液里的免疫,但还不够了解肺里的免疫。我希望在疫情发生后,能够有更多的人关注如何跨学科地解决肺脏疾病,因为这一定不是单一学科的疾病。
返朴:您在研究过程中,很多时候也会和医院、医生进行合作,您是怎么寻找这样的合作伙伴的?
汤楠:基本上都是我主动找医生合作的,他们都很愿意跟我合作,这种交流对我的帮助也很多,这方面我感觉我是很幸运的。
我们主要的合作伙伴是中日友好医院的医生们,王辰院士的团队。我特别愿意跟医生们进行交流,也很佩服他们。虽然工作忙,但他们对科研很有追求,看得出来是出于真心喜爱。比如曹斌老师,经常给我发他读到的文章,我们也会讨论具体靶点、具体分子、发病机制这些问题。
还有比如说和陈静瑜老师的合作,他是中国肺移植的第一人,掌握了各种终末期肺病的样本。虽然小鼠的肺脏和人的肺脏已经非常相似了,但是只依赖动物模型还是不能完全还原人体的疾病。在美国,研究者有条件获得健康人的肺样本,因为有许多健康的器官捐献者,你在获得驾照的时候,都会填写愿不愿意捐献器官,而国内的这类项目还非常少。
一开始也是我主动去找陈老师的,问能不能跟他合作。我自己并不满足于仅仅是发论文,因为发了论文并不代表你的发现就可以产生转化,或者能够说明人体疾病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过程。我比较注重人体的真实情况。和陈老师这样的医生合作,拿到适量的人肺样本,能帮助我们真正理解已有的动物模型,或者进一步认识已经发现的靶点,是不是一个可以继续往下推进的研究。
返朴:您从医生那边获得一些样品,可以解决一些研究问题,那么如果医生有一些临床上的问题和您探讨,会不会也能碰撞出新的研究问题?
汤楠:当然会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交流。一方面我自己是学医出身的,在医学院5年的训练很有用,熟悉查体、体征和各种术语,跟医生们交流起来基本上没有障碍。另一方面,我的临床经验毕竟还少,只有大内科的训练,和感染、肺纤维化等各个专科的专家交流起来,能了解和见识到更多临床问题。
我一直觉得应该加强 MD(医学生)和PhD(基础科研人员)的联系。有时候PhD的研究太基础,而MD太专业化,两者之间的鸿沟是很大的。医学生一开始就学生理、病理、药理、解剖,还有两年半的临床轮转,对疾病是有概念的。而MD的短板就是没有做过基础的科研,在具体疾病的研究上可能速度很快,但研究的深度上有时达不到开创性。而PhD如果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去了解过某种疾病,那么在研究小组里拿到一个表型,不知道它在生理上和病理上代表着什么,可能就会绕很多弯路。
返朴:您的团队关于新冠肺炎患者肺泡再生的研究也是和陈静瑜教授合作,这项研究是如何开展的?
汤楠:陈静瑜教授提供了肺的样本,是从两位做了肺移植的新冠病人身上换下来的肺。
人的肺再生过程一直没有找到标志物,比如说你拿到人肺组织,怎么知道它出现了再生?我们在前面的研究发现,人的肺泡干细胞再生过程中,会短暂地停留在一个状态,我们叫做中间态,它既不在肺泡干细胞里面表达,也不在肺泡的分化好的细胞里面表达,很难抓得住。但是单细胞测序就有这个本事,能够把这群细胞分离出来,我们就找到这群标志物了。所以拿到新冠患者的肺样本之后,我们就特别好奇,这里面会不会也存在肺再生过程?很高兴的是,我们真的看到了。
之前经常有患者和家属会写信或者打电话到我们实验室,说“老师,我得了新冠”,或者是“我爸爸得了新冠”,他们很担心不能恢复,有心理上的负担。我认为,虽然人肺再生不如小鼠那么稳健,但新冠患者康复之后,相对健康的肺都还是会自己慢慢恢复的。
我们也在努力发现可以促进和改善肺再生的方法,但问题在于,一方面你想去促进再生,另一方面,促进再生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干细胞激活和增殖的过程,可能诱发干细胞肿瘤,所以每一步走起来都如履薄冰。
汤楠笑言,新冠患者肺再生的研究在最初的投稿阶段还遭遇过“滑铁卢”。在完成了第一位患者样本的研究之后,团队迫不及待想要把新发现分享给全世界,于是选择了预印本平台bioRxiv,“我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想给大家打一针强心剂”。bioRxiv在收到文章后,反馈说因为涉及到人体组织,建议团队转投给medRxiv。谁成想,medRxiv以研究只包含一个患者样本为由,也拒绝了登载,“我们当时都傻眼了,什么时候预印本还要看重大意义了?”
幸运的是,Cell Research的编辑很看重这篇文章的意义,在团队完成了第二例样本的研究之后,文章顺利发表。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读博是一个工作”
能把被预印本拒绝的事迹当作笑谈,汤楠说,这证明自己进入了一个更开心的阶段, 能够接受一些事情了。这是从无数次的挫折中洗练出的,也是一名成熟的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品质。汤楠坦言,研究总是会遇到停滞的状态,要是想真正发现一些特别有趣的事情,这是必经之路。
面对初入师门的新人,汤楠是导师,也是合作伙伴,她相信平等的关系,相信互相帮助和共同成长,更喜欢学生“不服来战”。所有人都说,要把精力放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汤楠告诉学生,意义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定义的,研究者要追求自己的兴趣所在。
返朴:您认为哪些核心的能力或品质能够帮助一个人成为优秀的研究者?
汤楠:我觉得第一点是求真。我们实验室的项目很多都是倒三角形的发展过程,一开始形势不明确,你就会四处突击,尝试各种假设,但如果大方向真正走对了的话,到后面就越来越顺利,所以我觉得要尊重事实,追求真理。
第二点是情绪稳定。我的任务就是一定要有担当,既要保证我自己情绪稳定,有坚定的信念,同时还有责任去鼓励学生。他们毕竟还年轻,可能眼下的研究就是未来五年唯一的课题,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强有力的支持,这样才能走下去。
返朴:您现在也带很多学生,您是怎么和学生沟通、相处的呢?
汤楠:就是平等。因为我性格比较活泼,哪怕想摆出特别威严的样子,有点震慑力,我装了一天也装不下去了,哈哈!
我也带过一些医生,我了解医生受训练的体系是很严格的,比如查房的时候,走路的位置和顺序都是有要求的。但我和他们这么说,做医生需要听话是很正常的,因为那些约束和守则是无数人的生命和鲜血写出来的,你不遵守的话就可能导致感染、操作不当甚至死亡,但科学是不一样的,科学鼓励你发现意外,所以你要挑战。我很喜欢学生挑战我,对我说“我觉得你想的不对”。当然,如果挑战我的话,得先过我的逻辑这一关,过关之后,我们就有了讨论的余地。
我比较喜欢我原来的导师Gail 和 Randy的风格,“You do whatever you want.” 我也不喜欢每天给学生分配任务,更喜欢比如说每周开一次会。学生做独立研究项目的时候,需要帮助的话大家一起讨论,高年级的博士生和博后也会参与。具体的实验设计上我不会干涉特别多,但是出来的结果我会提非常多的问题,找到其中的漏洞。
看着学生们从“小白”成熟起来,获得成功,还是觉得挺骄傲的。我没有把自己放在上级、导师这样的位置上,学生们是我的合作伙伴,能够真正地帮助我,尤其是能谈得来的学生,就跟朋友是一样的。
图片授权:汤楠
返朴:现在好像有一种普遍的情绪,感觉读博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以前所期待的做学术的快乐不见了,您当年读书的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您怎么看待目前这种焦虑情绪?
汤楠:我们当年确实没遇到过,那时候心态纯粹很多。比如说我们那时候会有裸婚,只要互相喜欢,有一个小小的公寓住就会很开心。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工资也不多,和同学每天中午午休完,进医院上班的时候,院门口经常会有卖雪糕的,然后我们两个人过去看一眼就走,说今天又省了一块钱。
我那时候即使老大不小去当博后,也完全是出于对研究的热爱。现在的很多孩子可能会说,读博士是为了将来找一份好工作。我也不是要指责现在的孩子,毕竟时代不一样了,当年的快乐和现在的快乐不一样,压力也不一样。
很多孩子以为读博士是来上学了,其实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从博士生涯开始的这一瞬间就已经是在工作了。我会跟所有刚来的学生讲,读博士是对工作习惯的培养,自我学习能力和工作能力完全是两回事。比如有的人学习很好,不善于交流,但是工作的时候就是需要交流,要和你的导师交流,要寻求帮助,也要帮助他人,建立你的社交网络。我觉得科研真正做得好的人,并不是平时说的那种书呆子,反而都是很会交流的。他们有能力把自己的瞬间火花式的想法用具体的语言讲出来,还能让别人理解到,这是本事。
读博作为一个工作当然很清苦,因为博士生的工资还是比正式工作要低一些,但是你在拿到博士学位的同时,也拿到了人生最宝贵的经验,我觉得要把这件事情想透。
返朴:对于年轻研究者,有时候不确定眼前的道路是不是值得走下去、能不能体现出价值。关于怎么建立信念,您有什么心得体会吗?
汤楠:其实我在做研究生和博后的时候,也会对自己的研究有一些不确定。但现在我会跟学生说,不管你的文章发到了哪里,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有价值的,我一直强调个人的成长。即使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我还是会从每一个项目里学到新东西,不光是科学上的,还有对生活的、对人生的感触。很多学生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态度,但我觉得你如果把这件事情想通了,人的成长就是不断学习和积累的过程,可能心态就会好一些。
我觉得也许每个人内心都有拯救银河系的期望,想要当英雄,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即便读了博士,做了一段时间研究,其实很多人以后还是会改行的,但是自己学到的能力是不会丢的,人总会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价值——不一定是拯救一个病人,但是总是能够拯救某些人。
谈到未来的方向,汤楠说,还是想利用自己的长处,凭借对动物模型和对表型的深入理解,把肺的疾病模型不断建立起来。这样的研究意义重大,例如团队在去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特发性肺纤维化(IPF)的小鼠模型,为后续的药物研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机会。虽然用汤楠自己的话说,这个模型是“莫名其妙、歪打正着地给做出来了”,但我们深知,每一个意外之喜,都来自科研工作者在困难面前的“欲罢不能”。
参考文献
[1] https://doi.org/10.1038/s41422-020-0369-7
[2] Butler, J. P. et al. N. Engl. J. Med. 367, 244–247 (2012).
[3]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19.11.027
本文链接:https://www.bjjcc.cn/kepu/15913.html,文章来源:科普之家,作者:返朴,版权归作者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