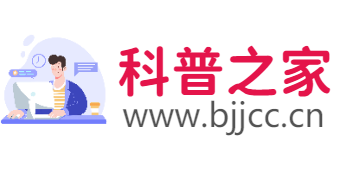抗击疟疾:不只有屠呦呦,这是五个诺奖都没打完的艰难战役
时间:2022-07-05 04:21:10 来源:科普之家 作者:科学声音 栏目:前沿 阅读:52
作者:李焱 刘永清(科学声音科普写作训练营第四期学员)
引1974 年 11 月,整个云南省阿佤山地区都笼罩在浓浓的雨雾之中。南腊公社的老支书撑着雨伞,一步一趋地跟在连夜赶来的李国桥身后,他尽量把伞往前伸着,想给这位远道而来的专家多遮点儿雨。
连续的阴雨让本来就不好走的乡间小道泥泞不堪。两人一前一后,深一脚浅一脚,急匆匆地往村里走。
老支书一边走,一边介绍着情况:“这才半个多月,就已经走了 8 个了。一会儿去的这家,男人前几天得病,歿了,现在女人也病了。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她家的娃儿可咋办。”
说话间,两人已经来到一个农户家门口。大门敞着,靠近门口一块门板上躺着一个女人,旁边不远的地上,坐着一个大约两岁的孩子。孩子脸上还挂着眼泪,显然是刚刚哭过。看见有外人过来,孩子本能地往母亲身边靠过去。女人似乎醒了一下,她的手指微微动了动,但很快又继续陷入了昏迷状态。
李国桥把随身的药箱卸下来,在女人身边蹲下。老支书却没有进屋,他撑着伞站在门外的雨地里。他心里想:“这半个多月,十里八乡的医生都来过了,药开了不少,也没看见有什么效果。这位李专家带来的药,真的能行吗?”
李国桥早就从老支书脸上看出了他的担心,他也完全理解老支书的心情。毕竟,现在村里流行的,可不是普通的传染病,而是人人谈而色变的疟疾。
史料图:李国桥(最右)
上世纪 40 年代,我国每年约有 3000 万疟疾病例,30 万人因此死亡。要知道,当时的中国人口也就“四万万”而已。算起来,当时我国的疟疾患病率高达 7%,死亡率高达 1%。难怪人们谈疟色变。那么,这次南腊公社感染疟疾的人能逃过一劫吗?李国桥医生的药箱中是否藏着什么灵丹妙药呢?
这就是本文要给你讲述的故事。你可能不知道,在人类与疟疾的战争中,已经产生了 5 个诺贝尔奖,但这场战争依旧没有打完。让我从头给你说起。
疟疾的病因疟疾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在我国最古老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疟疾的记载。古人认为,疟疾的起因是暑气和风邪的轮番侵袭所致。
无独有偶,西方人也把疟疾的原因归结在空气上。疟疾的英文词汇——Malaria,正是“坏”(mala)和“空气”(aria)两个词根的组合。但是,把病因归结为空气,正好说明了人类的无助。很显然,只有找不到真正的病因,才会让人去怪罪空气。事实也证明,所有怪罪空气的医学理论,都没什么实际用处。疟疾就这样在人类中肆虐了几千年。
1875年,31岁的法国军医拉韦朗[[1]](Charles Louis Alphonse Laveran)受命前往阿尔及利亚的军队医院工作。当时,疟疾是士兵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死亡率很高。拉韦朗经过观察,猜测疟疾很可能是一种由微生物感染而引起的疾病。于是,他一有空就把疟疾病人的身体组织放在显微镜下反复观察,希望能从中找到病原体。这件事儿一干就是好几年。
图:拉韦朗
1880 年 11 月,拉韦朗在患者的脾脏中发现了一些类似色素的深色组织。他敏感地觉察到,这些类似色素的东西,应该来自于患者的血液。于是,他找来新鲜未经染色的患者血液,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显微镜下的血液,对于拉韦朗来说无比熟悉。但是,这一次,拉韦朗在显微镜里看到了一些反常的东西。在大量红细胞的中间,似乎有一些细胞的形态不太一样。它们变成了镰刀的形状,还有一些红细胞颜色变暗,另外一些则带着深色的斑块。
第二天,拉韦朗给 200 名患病士兵采了血。他在 148 份血样中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拉韦朗非常兴奋,他大胆地推断,一些寄生虫寄生在红细胞的内部,它们才是导致疟疾的元凶。
12 月,拉韦朗向法国医学科学院提交了他的研究成果。但遗憾的是,他过于前卫的想法没能说服任何一位同行。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寄生在血红细胞中的小虫子,简直是天方夜谭一般[2]。
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的判断,1882 年拉韦朗来到了疟疾爆发的罗马。他仔细比对了很多健康人和疟疾患者的血液后得出结论,只有患者的血液中才能找到这种微小的寄生虫。拉韦朗把这种寄生虫命名为疟原虫。
这一次,详实的对比观察记录终于说服了同在罗马的研究疟疾的学者。很快,一向以固执著称的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也公开支持了拉韦朗的结论。巴斯德的支持让更多的科学家开始关注拉韦朗的研究,他的理论,终于成为了微生物学家们的普遍共识。
疟原虫的发现,让人类不再需要把疟疾归罪于腐败的空气。人类在饱受了几千年的痛苦折磨之后,终于打响了反抗疟疾的第一枪。
传播之谜造就前 2 个诺奖尽管对疟原虫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但仍然没有人能够解释:疟原虫是如何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1883 年,美国医生阿尔伯特·金通过大量观察发现,疟疾总是在蚊虫滋扰比较严重的地区爆发,于是提出了蚊子传播疟疾的假说。但是,根深蒂固的瘴气学说再次把这个假说引上了邪路。一些人认为,是蚊虫污染了饮用水造成了感染。还有一些人认为,感染是人类吸入了蚊虫污染过的池塘边上的灰尘。
1894 年,在印度服役的英国军医罗纳德·罗斯,他所在的部队也饱受着疟疾的困扰。罗斯最初认为,疟疾是一种肠道感染,病原体应该是通过污染水源的方式传播和感染的。这个错误的认识让罗斯白费了不少时间。幸运的是,罗斯当时有位非常厉害的搭档,名叫帕特里克·曼森。曼森在早年研究丝虫病的时候,就证明了蚊子是传播丝虫病的罪魁祸首。他提醒罗斯,蚊子很容易成为血液寄生虫传染病的中间宿主,应该把重点放在蚊子身上。
罗斯被说服了,他马上开始大量解剖蚊子。然而,印度当地至少有上百种不同的蚊子,而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疟疾的蚊子只有一种[3]。解剖蚊子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困难重重。罗斯的本职工作是一名医生,他对昆虫学几乎一窍不通。为了能够找到传播疟疾的蚊子,他就根据自己在显微镜下的观察,用土办法把蚊子分类。在他的实验报告里,会用灰蚊子 A、灰蚊子 B、花蚊子 C、花蚊子 D 这种方式给不同的蚊子命名。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灰色蚊子的名字叫做库蚊,而能够传播疟疾的花蚊子,名叫按蚊。
图:罗斯
后来罗斯还发现,鸟类的身上也有疟原虫,只不过这些疟原虫只能通过灰蚊子在鸟类之间传播。罗斯还用鸟类中流行的疟疾,设计了一个传播实验,最终发现了疟原虫在寄主体内的传播和发育史。
原来,按蚊是疟原虫的另外一个宿主。按蚊吸取病人血液的时候,疟原虫的雌雄配子就会跟随血液一起进入按蚊的胃部。紧接着,雌雄配子会结合成为会动的合子,这些合子会寄生在蚊子的胃壁上发育成卵囊,再生成大量可以侵入蚊子唾液腺的子孢子。在按蚊叮咬了人类之后,子孢子就会随着血液侵入肝细胞中增殖,产生出可以入侵血红细胞的裂殖子。这些裂殖子入侵血红细胞之后,还会继续增殖,其中的一部分就会分化成能进入蚊子体内的配子。
我刚刚说的子孢子、裂殖子这些名词,你不理解也没有关系。这些都是疟原虫在不同生长阶段表现出来的不同状态。每一种状态,都能与宿主的身体环境完美地匹配。如果人体的免疫系统比较强大,它们还会变成一种能够逃过免疫系统的休眠子,藏在肝脏细胞中逃过免疫系统的追击。
罗斯的厉害之处,就是证实了按蚊是疟疾的传播媒介,并且阐明了疟原虫的发育史。这一研究成果很快就得到了学界的普遍接受。既然知道了按蚊是疟疾的传播媒介,预防疟疾就有了有效的手段,那就是可以防蚊和灭蚊。1902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也因此颁给了罗斯[4]。
1907 年,发现了疟原虫的拉韦朗终于获得了诺奖。虽然这个奖的到来,比他的后继者罗斯还要晚了 5 年,但也算是对他开创性工作的追认。
这是人类抗击疟疾的战争中,产生的第一、第二个诺奖。
蚊帐的发明曾经与罗斯共同研究疟疾的曼森只获得了诺奖的提名,这让他有些不太愉快。离开印度之后,曼森回到了罗马的疟疾高发地区继续深入研究疟疾。
图:曼森
曼森发现,最多的蚊虫叮咬总是发生在人们熟睡的时候,他在最容易患上疟疾的季节让受试者使用蚊帐睡觉,然后记录和统计受试者感染疟疾的概率。实验证明,夜晚睡在蚊帐中果然可以大幅度降低患上疟疾的概率,蚊帐的确是一种简单而且有效的预防疟疾的方法。
但是,蚊帐只能在晚上提供保护,人们在白天也一样会被按蚊叮咬而患上疟疾。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2019 年,非洲面临疟疾风险的人中大约有 46% 得到了药浸蚊帐的保护,但非洲的疟疾病例和死亡数仍然居高不下[5]。平均每 6 个非洲人中就有 1 个患上疟疾。这还是 2019 年的数据,20 世纪初的时候,在欠发达地区普及蚊帐,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迫切需要能够治疗疟疾的特效药。
备受争议的第三个诺奖十九世纪初是一个连抗生素都没有的年代,对于生长过程极其复杂的疟原虫,人类几乎无计可施,只能靠碰运气的方式进行研究。
传说古老的印第安部落中,有用金鸡纳树皮研成粉末来治疗疟疾的方法。这种古方的治疗效果虽然很不稳定,但偶尔确实能救人一命。由于疟疾在全球的肆虐,早在 17 世纪的时候,这种治疗疟疾的方法,就以神秘古方的形式,在贵族当中偷偷流传。随着化学提取与分析技术的进步,人们逐渐揭开了古老秘方背后的奥秘。
1820 年,法国化学家佩尔蒂埃[6](Pierre Joseph Pelletier)和卡文图[7](Caventou, Joseph Bienaime),从金鸡纳树皮中提纯出奎宁。这是一种带有浓烈苦味的白色粉末,俗称“金鸡纳霜”。后来证明,奎宁正是金鸡纳树皮中抗疟的有效成分。于是,欧洲人开始在东南亚大量种植金鸡纳树,用于疟疾治疗。
奎宁虽然有效,但依靠金鸡纳树皮来提取,产量实在是太低了。大多数生活在疟疾高发地区的人们,仍然处于无药可用的状态。
蚊帐只能在夜晚提供保护,而特效药奎宁的产量又跟不上,那么使用杀虫剂灭蚊就成了最简单粗暴的方法。这就有点儿像“解决不了问题,但可以解决制造问题的人”的思路。
1939 年,瑞士化学家保罗·穆勒[8](Paul Hermann Müller)发现,一种名为 DDT [9] 的有机氯类杀虫剂几乎对所有的昆虫都有超强的杀灭效果。当时正处在二战期间,野外作战的士兵正饱受着疟疾、登革热和黄热病的困扰。美军果断地使用了 DDT 来对付蚊子,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由于用途广泛,效果良好,人们把 DDT 和青霉素、原子弹一起,并称为二战时期的三大发明。
图:穆勒
为了表彰穆勒在 DDT 杀虫效果方面的研究,诺奖委员会把 1948 年的生理学和医学奖颁给了保罗·穆勒。这是抗击疟疾的战役中,产生的第三个诺奖。
后来,由于对环境污染过于严重,DDT 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禁用。有人还指责说,为 DDT 的发现者颁奖,是诺奖委员会犯下的最大错误。但是,在 DDT 之后,人类始终都没能找到另外一种性能超越 DDT 的更环保的杀虫剂。两害相权取其轻。2002 年,世卫组织终于宣布,在疟疾高发的地区可以重新启用 DDT 来控制蚊子的繁殖。保罗·穆勒的诺奖我认为是应得的。
第 4 个诺奖——奎宁的热人工合成1944 年,又一个好消息传来。27 岁的美国化学家伍德沃德[10](Robert Burns Woodward)终于第一次实现了奎宁的人工合成。曾经高不可攀的抗疟神药,终于走下了神坛,开始大规模广泛的应用。1965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伍德沃德,表彰他在有机合成方面的重大贡献。这是抗击疟疾的战役中,产生的第四个诺奖,这一次,是众望所归。
图:伍德沃德
奎宁实现了人工合成,氯喹等同类药物也大量投入使用,疟疾这头凶兽似乎应该被“关进笼子”了。然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疟疾死亡率一度出现大幅度增加。因为疟原虫也在演化,它们在与药物的长期斗争中演化出了抗药性!人类亟需新一代抗疟药物。
第五座诺奖不只有屠呦呦先生中国也曾经是疟疾流行的重灾区。在国家领导人的亲自过问下,中国在 1967 年 5 月 23 日,为研制新的特效药召开了专门部署会议,并确定了 523 专项研究办公室。当时先后有 60 多个单位,500 多名科研人员加入了这项计划。
不过,那个年代,我们根本没有能力从分子生物学出发去研发一款新药。我们拥有的,其实只有战胜疟疾的必胜信心和一支庞大的吃苦耐劳的科研队伍。
1970 年 5 月,北京中医药物研究所的屠呦呦团队发现,用青蒿的乙醚提取物具有非常明显的抗疟功效。从药物研发总动员,到在动物实验中发现青蒿的抗疟作用,时间刚好 3 年。这在药物研发史上堪称奇迹。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青蒿素的雏形。
有人说,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找到青蒿素,靠的完全就是运气。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的是,在青蒿素被发现之前,我国的其他科研机构已经完成了超过 4 万种化合物和中草药的验药工作。其中几乎涵盖了能找到的所有古方。
即便是发现青蒿素之后,为了找到抗疟效果最佳的植物,科学家们立即集中优势力量,把国内能找到的所有菊科植物又排查了一遍。最后,云南药物研究所的的罗泽渊团队从黄花蒿中提取出了抗疟药单体,才把青蒿素的提取植物最终定了下来。
图:黄花蒿
这是一次超大规模的验药行动,是对抗虐药物的一次地毯式的大排查。这次验药行动,效率之高,规模之大,在全世界都是史无前例的。如果没有高水平的科研管理能力,这样一个不亚于建造大型水电站的工程是根本无法完成的。
1970 年之后,由于疟原虫对老牌抗虐药物奎宁的抗药性逐步显现,我国的疟疾死亡率开始陡然上升。青蒿素迫切需要进入临床应用阶段。1974 年 5 月,长期战斗在抗疟一线的李国桥团队临危受命,开始了青蒿素的临床实验阶段。这就有了本文开始的那一幕。
图:李国桥
李国桥面前的这个女人,患的是最严重的脑型疟疾,现在已经昏迷不醒。如果用奎宁这样的常规抗疟药物进行治疗,很有可能会导致患者死亡。在之前的临床病例中,李国桥还从来并没有遇到过脑型疟疾,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李国桥只能用青蒿素尝试治疗。
青蒿素的治疗结果出人意料地好。女人在服药之后,很快就脱离了昏迷状态,20 个小时之后,血液中 95% 的疟原虫都被杀死了。随后,越来多的临床数据证实青蒿素可以安全、速效地治疗疟疾[11]。人类在抗击疟疾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青蒿素联合疗法在世界范围内被迅速推广应用,挽救了无数疟疾患者的生命。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颁给了屠呦呦,表彰她在疟疾新疗法上的创新和发现。这是抗击疟疾的战役中,产生的第五个诺奖,也是我国医学工作者为世界医学做出的宝贵贡献。
从 2017 年到 2020 年,在青蒿素的加持下,我国已经连续四年没有发现本土疟疾病例,这或许就是阅读本文的你对疟疾这个词有些陌生的原因所在。人类对抗疟疾的战争,露出了胜利的曙光。
到此你是不是认为,人类与疟疾的战争就快要结束了?
哪有那么简单,抗疟这事儿远没有结束。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句成语很有意思,可以根据需要正反着用。
重在防疫你可能会对新冠病毒全球感染数突破 1 亿这个数字感到吃惊。但你可能不知道, 2019 年全球共报告的疟疾病例达到 2.29 亿,死亡 40.9 万例。这比起 2016 年的数据,并没有显著减少。2020 年,在非洲比较贫困的地区,因疟疾死亡的人数甚至远多于新冠肺炎导致的死亡。为此,2020 年 11 月 30 日,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呼吁,对疟疾的警惕不能放松。
在世界上基本消灭疟疾的国家里,只有我国是人口大国。在我国广西云南等地的边陲农村,生活远远算不上富裕。但是,我们硬生生地把疟疾的本地病例降到了零,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的方法,说起来你肯定不陌生,那就是 3 分靠治疗,7 分靠防疫。
我国最经典的疟疾防疫方法,叫做 137 模式。“1” 就是地方卫生所在收治疟疾病人后,必须在 1 天内上报病例。“3” 就是上级医院必须在 3 天内复核病例。“7” 就是县级医院必须在 7 天内完成密接人群的检测和调查,同时杀灭周围可能传染疟疾的按蚊。而作为患者本人,则会被隔离在一个不可能被蚊子咬到的地方接受治疗,直到治愈为止。
我们的另一项创新防疫措施,叫做大规模药物管理。这个概念就是疟疾临床第一人,李国桥医生提出的。在疟疾呈现爆发态势的村子,他会采用群体给药的方式,让该地区所有村民一起服药,以此来消灭所有潜伏在人体内的疟原虫。服药之后,整个区域内的居民就会形成一定时间的群体免疫,从而达到彻底消灭疟原虫的效果。
从 2017 年到 2019 年,每年都有 2000多 例境外输入的疟疾病例。正是边境地区的一个个村镇,帮我们顶住了防疫的压力。
2020 年的新冠疫情,让全中国人都知道,我国有着世界领先的传染病防疫体系。但大家所不知道的是,优秀的防疫体系背后,是科学与管理的共同进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道德文化,以及负重前行、不畏牺牲的医者英雄们。
信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Louis_Alphonse_Laveran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825508/
郭奕玲 沈慧君 蚊腹中的发现_记罗斯对疟疾病源的研究 2008-09-29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30a6c020101heol.html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malar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ierre_Joseph_Pelleti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seph_Bienaim%C3%A9_Caventou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ul_Hermann_M%C3%BCll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D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Burns_Woodward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82)90268-9/fulltext
本文链接:https://www.bjjcc.cn/kepu/15932.html,文章来源:科普之家,作者:科学声音,版权归作者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