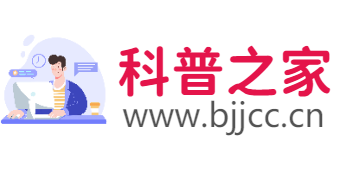科技干预与人类困境:论王晋康科幻小说“新人类四部曲”
时间:2022-07-06 12:44:44 来源:科普之家 作者: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栏目:科幻 阅读:120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科技成为人类探索与改造世界、解决当下困境与规划未来发展的全球性议题。1988年,第十届国际人道主义和伦理学会世界大会通过的《相互依存宣言:一种新的全球伦理学》(The Declaration of Interdependence: A New Global Ethics)指出:“我们的地球是相互依存的民族-国家构成的,无论在这个星球的某一部分发生什么,都会影响到其余的部分……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世界共同体都有高度的责任。”[1]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也愈来愈被世界多数国家所接受。但由科技发展引发的连锁效应,必然会对现存人类社会体系和固有思维方式造成挑战。
科幻小说作为一个兼具科普性与文学性的文学门类,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其独特的范式;科幻小说家既要对当下及未来技术的发展有预见性,同时也肩负着传递科学信仰、固守道德伦理价值的使命。科幻小说是科学未来与现实生活的锚点,许多科学设想都率先在科幻小说中提出,许多质疑和冲突也在科幻小说里爆发,科学的成果在实验室里收获,但假想的验证却可以在科幻世界中发生。恰如有学者所指出:“科幻小说总是在现实社会之外,建立一个或数个虚拟空间。虚拟空间是现实社会的参照对象,总是扮演着现实社会的指引者或者对抗者。”[2]在刘慈欣、韩松、王晋康等科幻小说家不遗余力的推动下,当下中国科幻小说凭借宏大的视野和细腻的人文反思,在文坛可谓异军突起。当刘慈欣《三体》蜚声海内外后,中国科幻也打破了大众对它的刻板印象,掀起了一股科幻小说创作与研究的小热潮。
1993年出道的王晋康,凭借自身的科学素养和创作热情,在其漫长的创作生涯中推出了《逃出母宇宙》《天父地母》和《时间之河》等佳作并多次荣获银河奖,七十高龄依旧笔耕不辍。在其“新人类四部曲”《类人》《豹人》《癌人》《海豚人》中,面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困境,科学家们选择用基因编辑手段对个体和人类种群的未来加以干预,无论是利用特殊细胞还是在人类遗传信息中加入其他物种的片段,小说中这些科学家们都扮演了上帝的角色来操控人类的命运。而现实中,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埃马纽埃尔·卡彭蒂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和詹妮弗·A.杜德纳(Jennifer A. Doudna),也是因她们开发了一种基因编辑的方法:通过一种“剪刀”(Cas蛋白质)来删除病毒基因,留下良性基因,并通过将病毒基因的一小段带回CRISPR(短回文重复序列)资料库,从而在面临相同病毒的再次侵袭时能够进行快速匹配和消灭。在当下,基因编辑早已超过了外源物质随机插入宿主基因的初级阶段,能够完成对定点识别编辑。这是否也验证了科学和科幻文学的互文?当基因编辑的人体应用在现实中备受争论时,科幻文学早已在另一个空间完成了对假设的应用和验证。作为中国基因主题科幻创作的第一人,王晋康在关注科技介入人类基因工程的理论性和可行性时,也将其中的伦理问题和情感抉择纳入其中,从而在严肃的科技讨论外添加了一抹人性的变量,形成更具张力的艺术魅力。
一、科技干预与人类生存困境
归根结底,科技是为人类服务的,而人类文明想要延续,首要解决的就是生存问题。在浩瀚的宇宙中,地球是人类已知的唯一能够孕育自然生命的摇篮,也正是这种唯一性赋予了人类恐惧未知和渴望探索的矛盾特性。正如罗伯特·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所说:“传奇世界和经验世界之间的严重脱位表现在不同方面,最明显的一种方式,是人们为了增加叙述规则的力量而置自然规律于不顾,这其实是人们以表达愿望和恐惧的形式所体现出的人类心灵的映射。”[3]地外威胁和天文灾变是当下最有可能在一夕间毁灭地球的因素。作为地球的主宰,人类掌握了万物的生杀大权,无论是微小如蚂蚁还是强壮如黑猩猩,它们看似森严牢固的生存体系在人类的介入下都不堪一击。那么,当高等智慧发现人类文明时,是否会复现刘慈欣“黑暗森林法则”中提到的情况:一旦某个文明被发现,就必然遭到其他文明的打击呢?
王晋康的《海豚人》《类人》也提到了类似的高等智慧,这些力量是相对中立和友善的,但人类对其态度却相当复杂。在《海豚人》中,这些地外智慧对人类文明中的高等动物进行智力提升,并消除邪恶力量、维护宇宙平衡。在《类人》中,作者用蜜蜂和养蜂人来类比人类对“神”(更高智慧生命)的感知。司马林达说:“老张你就是高踞于蜜蜂社会之上的神,你干涉了蜜蜂的生活。比如:你带它们坐上汽车到处追逐蜜源,你剥夺了它们很大一部分劳动成果供人享用,你帮它们分群繁殖,建造新蜂巢等等。但蜜蜂们能感觉到这种‘神的干涉’吗?”[4]102小说中的超智慧体以电子信息的形态存在于网络中,唯一的生存目的在于思考和探索,并向人类提供所需要的低级服务;而人类受困于智力阈值的“管道”内,如蜜蜂一般难以觉察到上级智慧的存在,只能将“干预”现象归结为神迹、命运或巧合,纵使心有不甘也只能做出如“蜜蜂糟践养蜂人补充的外来蜂蜜”一般的“孩子气的放纵”。
《类人》中低级智慧能够察觉高级智慧的唯一途径在于高级智慧的主动显现。已经融入超智慧体的司马林达通过电力线进入断网的电脑,向宇何剑鸣和齐洪德刚表明身份。但王晋康一个有意思的设定在于,超智力体这个高于人类的智慧存在本身,是由人类创造并且寄居在人类社会中的:“有没有比人类更高级的智力呢?有,就是电脑。单个电脑是无意识的,只能执行人的命令,单个电脑就相当于人脑的单个神经元。但只要达到某一临界数量,就会自动产生‘我识’,产生超智力。而且,由于它们没有人类大脑的种种限制,最终将会超过人类智力,这点毫无疑问。”[4]167因此,超智力体是一种群体智慧,它和人类的关系并不简单地雷同于养蜂人和蜜蜂(养蜂人不由蜜蜂创造),而是构成了一种循环——人类创造网络智慧,网络智慧干预人类发展。王晋康同时还设计了另一要点:“养蜂人的谕旨:不要唤醒蜜蜂”[4]57。因为司马林达对人类社会的直接干预在于,他对超智慧体融入得并不彻底,真正的超智慧体不会主动激发人类对他的察觉。知晓了自己的命运掌控在超智力体手中的人类(即这群被唤醒的蜜蜂),在解决了自己同智慧体的内部矛盾后会如何看待超智慧体?是反抗还是妥协?或许又要回到不同智慧与文明的角逐问题当中。显然,如果以自由为准绳,即使再友善的高等智慧,当其介入人类生活时,也会让人类心理产生微妙的变化。
相较于人类对高等智慧生命的幻想,天文灾变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则更为现实。王晋康在《海豚人》中就描述了这样一种天文灾变的恐惧:“近距离超新星爆发。宇宙射线暴和紫外线暴。地磁场消失,电离层消失。臭氧层消失。超剂量辐射,地面上的所有人和动物将在几天内死亡。”[5]90自恃强大的人类在广袤的宇宙面前微不足道,一个小小星球的爆炸就能毁灭人类千年来的文明。在这样的全球性灾难下,任何地面上的物种都难逃一死,如何将人类基因、文明和历史加以传承就成了幸存者的当务之急。《海豚人》中,那些在辐射爆发时藏匿于几百米深的岩下和水下的幸存者们,难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去维持人类种族的繁衍,于是改革者拉姆斯菲尔和覃良笛开始在南太平洋的群岛上对人类的基因进行改良,他们通过人工授精和基因嵌入术让人类后代的身体长出青蛙的脚膜,从而适应海里生活。实际上,覃良笛比拉姆斯菲尔走得更远,突破了种族的限制,将人类智慧传递给海豚,让人类文明在海豚人中继续延续。《海豚人》中提出的假设给了人类在面对天文灾变后保存文明的一种生存可能,但同时也引发一个思考:当其他物种或生命形式继承了人类的智慧时,他们的存在形式能否代表人类文明的延续?
二、科技干预与人类发展困境
除了人类必须直面的生存困境,地球本身在为人类提供资源的同时也限制着人类未来的发展。人类拓展和改造世界的想法是不会停止的,这其中有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渴望拥有更多繁衍机会的生物本能,也有人类作为地球上唯一智慧生命渴望征服更多领域的心理因素。从荒漠到极地、从地壳到宇宙,人类在不懈努力下一次次突破空间极限,但有些问题只能求助于科技手段进行干预。首先是资源困境。人类作为食物链的顶层猎食者和生物圈的支配者,通过开采矿产资源、圈养其他生物等途径来满足自己生产建设的需求,但目前唯一的“生命摇篮”——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为了文明的发展,人类必须通过科技进一步对自然进行开发并竭力寻找更多替代性能源,但人类的发展速度终究和资源的储备量成反比,不加限制地发展必然让地球资源走向枯竭。
如何在文明发展和生态保护中取得平衡,《海豚人》给出了一种可能:尊重本能、顺从自然。在被覃良笛冷冻之前,拉姆斯菲尔是一艘核潜艇的舰长,也是人类力量的强力体现——拉姆斯菲尔一声令下,几千万人口的城市瞬间就会灰飞烟灭。沉睡百年的拉姆斯菲尔从本质上来讲并没有改变对人类的智慧与武力支配的沉醉,甚至为了确保海人的统治地位而意图密谋推翻海豚人的统治,但当拉姆斯菲尔失去至亲独自面对“窝格罗”时,他终于明白,不管是高级智慧还是低级智慧,盲目追求发展只会给文明染上污点:“文明和科技向上发展时,有些丑恶是避免不了的,连窝格罗也做不到这一点。历史走了几千万年,只是把两个猿类王者的互相残杀放大成两个宇宙级文明的互相残杀。仅此而已。”[5]259通过和窝格罗的对话,拉姆斯菲尔洞见了漫长的历史和宇宙各种族的诞生和湮灭,也理解了海豚人为何能够拒绝无限智慧和力量的诱惑,保持和平、原始生活的选择。
海豚人凭借智慧驯服了生物天敌——虎鲸,但并没有限制虎鲸对海豚及其他生物的自然捕食,严格恪守生物圈的秩序。针对特殊情况,海豚人的创造者覃良笛还发明了“圣禁令”:“‘圣禁令’是对海洋所有生灵颁布的。你知道,海豚人已经建立了在海洋中的绝对权威,但平时他们并不禁止虎鲸、鲨鱼等对海豚人的捕食,不干涉它们的‘天赐之权’,但只要颁布了‘圣禁令’,那么在禁令所限的区域内和时段内,就不允许对海豚人的侵犯了。这种‘圣禁令’是十分权威的,但使用很谨慎……”[5]123同样具备人类智慧的海人和海豚人,前者更多地继承了人类的外貌,但也无法跳脱出人类贪婪、复杂的劣根性;后者虽然保持着海豚的样貌,却选择谨慎地处理智慧和力量,从而真正实现了对技术的合理运用,进而保障种族的可持续发展。
另一个发展困境是人类的生理局限。无论是人类的体能、智力还是寿命都有着物种发展的上限,当人类想要去突破这些先天的局限时,就必须借助其他手段来改变自己的基因。在传统观念中,基因和遗传是上帝的密码,人类凭借科学技术找到了这个密码,是否意味着人类可以跳出种族的壁垒与基因的缺陷,将自己改造成一种“超人”?在“新人类”四部曲中,王晋康设想了基因技术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影响。《癌人》中由癌细胞培育克隆出的“癌人”,拥有强大的修复力与生命力;《类人》中由无生命物质组成的“类人”,拥有和人类相同的外貌和智力;《豹人》与《海豚人》中,将动物基因与人类基因编辑重组的“豹人”和“海豚人”,则分别拥有着超强的力量与智慧。但这些技术在带来变革的同时也引人深思。《豹人》中拥有非洲猎豹基因的谢豹飞,成为田径场上的天选之子,田联主席的赞美表达人类对“超级飞人”的惊叹:“不少专家论证过百米跑的生理极限,有人说是9.6秒,有人说是9.5秒。没有人料到,21世纪才过了十几年,这个纪录就大幅度地提高到9.39秒!从此我再也不相信专家和权威的断言了!”[6]64
在制定了最科学的训练方案,配备了最先进的运动装备后,人类的田径成绩依然被生理局限所制约。所以,当一个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的田径选手出现时,他的成功不仅仅属于他个人,也属于全人类:“对于鲍菲·谢而言,这只是短短的100米;但对于人类来说,却跨越了几个世纪。”[6]63基因嵌入术对于体育竞技水平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但贸然改变人类的基因编码并非没有风险。“豹人”在拥有体力和速度的同时,凶残与嗜血也附着于他的本能中,月圆之夜,谢豹飞无法抑制本能,失控咬死了自己的未婚妻田歌,一桩佳偶天成的喜剧变成了一个谋杀与复仇的悲剧。“世上万事万物都处于微妙的平衡中,人虽然没有猎豹跑得快,没有大猩猩孔武有力,但人的体态实际是在人的环境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好平衡。如果一味增强某一方面,比如增强奔跑能力,这条路会终结于何处?最终只有把人变成猎豹!”[6]149最后的法庭审判,律师这番话也引发了人类对科技的反思,人类利用基因嵌入技术想要吸收其他物种的优势、弥补能力上的短板,但恰恰是这些DNA遗传上的细微差异决定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异,也决定了人性与兽性的不同:“因为这些灵魂或本能是同物质结构密不可分的。不可能把人性或兽性与它们赖以存在的基因剥离,就如同你不能把‘锋利’与刀刃分开。”[6]203
小说《癌人》和《类人》也从不同角度对基因改造进行了反思。《癌人》中由癌细胞克隆出来的小女孩海拉拥有身体修复的能力,器官商人们就试图培育出和海拉相同的“癌人”成为供体,源源不断地为有需求的人类提供器官。由于癌细胞疯狂增殖的特性,海拉受伤的胳膊持续复原增长,必须定期去医院截断,在海拉遵循人类繁衍的过程成功怀孕后,癌细胞借助胚胎细胞的扩散最终摧毁了海拉,人类想要借助癌细胞获得廉价器官来源的想法也被彻底打消。“人类的异化是缓慢的、渐进的,但是,当人类变革自身的努力超越‘补足’阶段而迈入‘改良’时,人类的异化就超过了临界点。”[6]226科技是助推人类发展的利器,但如果仅仅为了发展科技就罔顾客观规律,只会让人类陷入更深的发展困境。
三、科技干预与伦理道德困境
任何科技的发展都不能逃避道德伦理的制约,如果说硬件配备决定着科技发展的上限,那么道德伦理就坚守着科技发展的下限和底线。在人类认识到自然现象和生命繁衍的规律之前,都不约而同地将无法解释的现象归结于“神”。自达尔文的进化论一出,人类逐渐脱离宗教的制约转而开始研究细胞和遗传。但是,人类从上帝手中接过生命起源的“接力棒”,是否意味着人类完全破译了生命的密码,拥有创造和改造生命的权力呢?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基因工程从未停止过对生命的探寻,从试管婴儿到克隆羊多莉,从胚胎繁殖到基因编辑,人类对生命研究的进程在一步步深入,与此同时也在科学和道德的钟摆中徘徊。
2018年,“用基因编辑干细胞治疗艾滋病”的报道登上了中国科技新闻的头条,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和他的团队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宣布,他们通过基因编辑将一对双胞胎的基因进行修改,这意味着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消息一出,立即引发舆论哗然:有人说贺建奎是天使,通过基因技术将人类从艾滋病的死亡阴影中拯救出来;但也有人说,贺建奎是魔鬼,不计后果地改变了生命的形态。贺建奎最终因为违规操作被批捕,但由此引发的道德争议却一直延续下去。当基因技术越来越先进,对人类社会的干预也逐步增强时,该用哪一种标准来衡量科技的底线?如果真的诞生了新的物种,又该用哪一款法律条文来辩护其合法性?
科技与道德遭遇的第一重困境,在于如何平衡科技的干预和人类的私欲。“西方文学中人类对‘人造智能生命’的态度,大体经历了从拒绝接纳,到奴化控制,再到交融共生的三个发展阶段。”[7]但想要破除偏见走入交融共生的第三阶段,人类要跨越的不仅是技术、习惯上的难题,更是人类固有的劣根性。在《癌人》中,PPG公司克隆出的第一个“癌人”海拉,使用了保罗祖母的癌细胞,由董事长罗伯逊先生的女儿苏玛的子宫孕育;但即使是出于对女儿的愧疚,罗伯逊先生和他代表的利益集团依然不愿意承认这个由正常人类子宫孕育的生命拥有和人类相同的身份和权力,而仅仅打算将海拉作为一个慰藉苏玛的玩物。讽刺的是,PPG公司还试图利用一部名为《不死的众神》的科幻小说来给大众洗脑,增强公司获得使用癌人的合法性和舆论支持。
这是伊恩的大胆策划,他正是从保罗此前的作品中获得灵感,想以科幻小说来传达公司的想法。小说中实际包括了PPG公司的核心计划,而刚才看的公司声明只不过是官样文章。小说中描写2015年的人类已经过上奥林匹斯山诸神的生活,他们的寿命仅以大脑寿命为准,因为其他部件都可以非常方便地更换,就像汽车更换轴承和油封等易损件,而且换上的心脏或肝脏都是“永不磨损”型,即使大脑的局部病变也可修补,器官备件则来源于人类圈养的数量众多的癌人族。伊恩希望它能“唤醒人基因中的自私本性”,从而“在人类现今的道德禁锢中劈开几道裂缝”[8]。企图混淆大众道德观念的公司有着自己的逻辑:一边是唾手可得的额外100年寿命,以及终生保持青春活力;一边是逻辑混乱、不知所云的生物伦理学戒律。公民和议员们该投谁的票?基因公司敢于挑战传统伦理道德,正是利用了人性的自私与贪婪。人类既然能够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去圈养和使用其他物种,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自然也能够被说服去剥削癌人。
科技与道德遭遇的另一重困境,在于人与非人的界限。基因技术的发展为克隆人和人造生命的诞生提供了技术支持,但这些新人种的权利和合法性并没有得到保障。《癌人》中海拉被剥夺了成为正常人的权利:“我相信,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不会把一个单细胞生物的后代称作同类。”同时她还被宗教人士和极端势力围剿,被迫在重回人类社会后再次藏匿,她和印第安人、克隆人一起在地下建立了自己的海拉王国,通过人造子宫繁育自己的后代。虽然海拉怀孕时癌细胞的急速增殖摧毁了她的机体,但是海拉想要受孕、繁育后代、建立自己族群的渴望,反映出她和人类共通的情感。面对海拉的存在,创造她的人类是拒绝和排斥的,这也导致了海拉王国和人类走向对立面。
《癌人》和《类人》共同反映了人造人在正常人类社会的尴尬处境。在小说《类人》中,人类与类人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除了没有指纹,类人在外貌和心理上与正常人类没有任何不同,但是却被当作物品严格监管。类人没有结婚和繁衍后代的权利,在一定年限后随时可以被主人销毁。日积月累,这些诞生于生产线上的类人形成了谨小慎微的性格,割舍了自己的情感与欲望,完全服膺于人类的统治。人类中也有中立或同情类人遭遇的群体,他们在相处过程中对类人产生了情感,但当他们真正面临人类权利被分割、子孙后代在各方面都要和类人竞争时,也犹豫不决。当科技开始干预生命时,人类所依靠的伦理道德和传统观念正不断动摇。一旦这股力量跳脱人类的支配,转而对人类形成威胁,谁来对悲剧的后果负责?或许诚如《豹人》中在法庭上辩护的律师所言:“那个妄图代替上帝的人才是真正的罪犯,因为他肆意粉碎宇宙的秩序,毁坏了上帝赋予众生的和谐和安宁……他必将受到审判,无论是在人类的法庭还是在上帝的法庭!”[6]227
四、结语
“科幻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科学思考,有着更多的质疑和批判,这是当代世界科幻小说的主流意识,中国作家们也融入其中。”[9]科幻作品与现实的关系是微妙的,它绝不简单地以“艺术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一言以蔽之,科学和幻想这两个重要因素互为表里,现实中的科技实体为小说家们提供灵感的温床,同时他们又借由个人生活经验展开合理的想象,这就要求科幻小说家必须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创作想象。作为文学家族中的一个类别,科幻小说还需要完成启蒙和审美功能的大众期待,要求科幻小说在进行科学说理的同时兼顾读者的阅读体验。
反观王晋康的“新人类四部曲”,以科技工作者的专业眼光来看它固然有瑕疵,如对基因编辑的具体内涵只是简单带过;但值得探究的是,作为文学作品,它将我们重新带回全人类最迫切关注的命题——“未来”。正如前文所述,无论是生存、发展还是伦理,人类文明都不可避免地遭遇抉择和挑战,地震、海啸、病毒……这些灾难愈加频繁地爆发就愈加引发人类的恐惧和思考: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借助科技做些什么?怎么做,才能突破困境?即使真的成为“新人类”,那些我们无法丢弃或不能丢弃的人类本质又是什么?或许这些正是王晋康科幻小说真正带给我们去进一步关注和讨论的命题。
通讯作者:邓艮,西安外国语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参考文献:
[1] 保罗·库尔兹 .21 世纪的人道主义 [M]. 肖峰等,译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1998.
[2] 汤哲声 . 论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思维和边界 [J]. 学术月刊,2015(4):128-134.
[3] 罗伯特·斯科尔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阿瑟·B. 艾文斯,等 . 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 [M]. 王逢振,苏湛,李广益,等,译 .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4] 王晋康 . 类人 [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5] 王晋康 . 海豚人 [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6] 王晋康 . 豹人 [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7] 吕超 . 科幻文学中的人工智能伦理 [J]. 文化纵横,2017(4):45-55.
[8] 王晋康 . 癌人 [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9] 刘媛 . 论中国科幻小说科学观念的本土性特征 [J]. 文艺争鸣,2016(5): 138-142.
(排版:张馨木 编辑:齐钰 审定:邹贞)
本文链接:https://www.bjjcc.cn/kepu/34527.html,文章来源:科普之家,作者: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版权归作者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