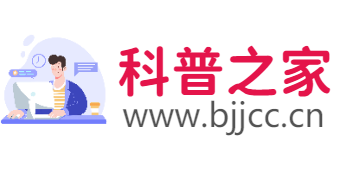论晚清科幻小说中“物”的功能化想象
时间:2022-07-06 12:45:03 来源:科普之家 作者: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栏目:科幻 阅读:399
突破现实空间束缚、憧憬异域世界的幻想传统古已有之。《山海经·海外西经》《博物志》都提及了由奇肱国氏制作的可以离地的“飞车”,《抱朴子·内篇·杂应》有“或用枣心木为飞车,以牛革结环,剑以引其机”的想象,《拾遗记》《搜神后记》等书中也都涉及了对异域空间的想象。明朝的民间发明家万户甚至努力将幻想落实到科学实践,在1400年左右试图使用风筝加上火箭的助推力飞上月球,最终却因火箭意外爆炸而以失败告终,也为此付出了生命。在新旧文化交替的晚清时期,憧憬异域空间这一幻想传统以科幻小说的形式得到延续。但与古人幻想方式不同的是,《月球殖民地小说》《电世界》《新石头记》《新野叟曝言》《女娲石》等一大批晚清科幻小说中的想象空间书写诞生于西方殖民势力裹挟着政治科技文明强势入侵的时代背景之下,作家因为受到强烈的意识形态诉求影响而将希望寄托于想象中的科学技术发明成果上。
在晚清科幻小说中,作为先进科学技术掌握者的发明家们使用先进成果带来改变社会现实的便利效果。这些科技成果和发明以一种只存在于想象层面的“物”的形态参与晚清科幻小说叙事,其强大的功能往往令阅读者瞠目结舌。达克·苏恩文(Darko Suvin)将科幻小说表现想象空间的特征描述为“一种发达的矛盾修饰法,一种现实性的非现实性,要表现人性化的非人类之异类,是根植于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世界’”[1],即科幻小说中的想象空间并非完全脱离于现实生活,而是依附于现实世界的同时又在读者认知层面显示出陌生化特质的“另外的世界”。但在晚清科幻小说身上,所谓的想象空间似乎只是由一个个技术制造出来的想象之“物”拼凑起来的集合。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晚清科幻小说中关于空间的想象就是关于“物”的功能化想象。这种功能化想象既体现在片面表现科学技术发明如何便捷有效的具体内容层面,也反映在小说家以科技之“物”的功能化想象宣传科技救国思想、表现现实关切情结的主题层面。
一、想象之“物”性能的无限夸大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物体系》(The System of Objects)中讨论了后现代消费语境下“物”的存在方式,以及人和物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面对功能物,人会变得失去功能、不理性、主观,变成一个空洞的形式,对功能神话,和世界炫人耳目的效率相关的幻想投射开放自身。”[2]鲍德里亚所阐述的“功能物”概念主要是指现代机械技术的强大力量对人的生存方式的影响,乃至对整个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异化作用。而在晚清科幻小说的具体语境中,小说家所想象的“物”虽然只存在于他们的观念层面,但在表现科技之“物”所制造的便捷效果意义上也体现出片面强调功能而忽视使用者的极端倾向。虽不能说小说中的人物已经完全失去自己存在的价值,但至少在描绘想象之“物”功能如何强大时,他们主要是作为感受“物”的功能的佐证材料而存在。这也是为何晚清科幻小说中的人物要么像《新石头记》中的贾宝玉一样在“文明境界”中处处学习和感受新科技、新政治缔造的美好幻境,要么便是像《新法螺先生谭》中的法螺先生那样凭借“脑电”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他们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为了表现想象之“物”本身功能的强大而服务,如何展示人物本身的内在性格和精神世界则并不是晚清科幻小说家会关心的问题。
晚清科幻小说中出现的对理想交通工具的想象同样十分突出地体现了功能先行的特征。陈平原指出,小说家们对理想交通工具的了解多来源于“出使官员的海外游记、传教士所办的时事和科学杂志、突出平民趣味的画报、古来传说被激活和重新诠释等等”[3]。《空中战争未来记》的创作灵感便是包天笑在《点石斋画报》上看到画师“画出来的是有帆,有桨,有舵,还装上了两翅膀”[4]的飞艇形象,因此激发了关于想象飞翔的兴趣。但这种以一知半解甚至道听途说性质的科学知识接受程度来进行科幻小说创作,小说结构的缜密性和科学逻辑的严谨性显然无法保证,科幻小说家所想象出来的事务经常与科学观念背道而驰。《空中战争未来记》中乘坐空中飞船上升到一定高度便可有助于身体健康,“在此空中十二小时,以至二十小时,凡一切肺病,咸足治疗,故乘此空中飞行船、翱翔天空,藉以疗治肺疾者甚多也”[5]。同样,在《月球殖民地小说》中,玉太郎发明的交通工具“气球”不仅厨房、卧室、天文台各种设备齐全,而且飞行速度快到片刻就可以飞越大半个地球。小说第十八回写气球飞到南寒带,玉太郎因为担心受伤的鱼拉伍受不了寒气又把气球开到北温带过夜,“那气候竟是立刻不同,一处像在隆冬光景,一处像在初夏光景;一处是寒风霍霍,一处是和风拂拂”[6]。包天笑、荒江钓叟等晚清科幻小说家想象出来的这种完全可以依照主人公意愿和需求进行调整的交通工具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科学合理性的范畴。
与只注重功能而忽视科学合理性的“飞艇”“气球”类似,《新纪元》的作者碧荷馆主人借人物之口将科技发明与仙魔斗法使用的法宝画上等号,指出“今日科学家造出的各种攻战器具,与古时小说上所言的法宝一般,有法宝的便胜,没有法宝的便败。设或彼此都有法宝,则优者胜,劣者败”[7]。小说中出现的“化水为火法”“行轮保险机”“海战知觉器”“洋面探险器”“流质电射灯”“水上步行器”“避电保险衣”等各种军事武器和科学发明虽然也涉及化学、光学等基本科学知识,但都只是采取标注发明时间、地点、功用,却漠视科学原理描写的介绍模式,往往是简单介绍几句之后便进入美好幻境的大段铺陈叙述当中,从此不再提及。类似《新纪元》中的军事武器这样的想象之“物”在晚清科幻小说中随处可见,如《女娲石》中的“电马”,《新法螺先生谭》中的“脑电”,《新石头记》中的“飞车”等。这些发明在小说中都已经是一种完成时态,读者能看到的只有这些发明者高超的智慧,以及发明成果带来的近乎无所不能的便利效果。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科技发明功能的无限制夸大是晚清科幻小说中的想象之“物”唯一的存在方式。读者在进入晚清科幻小说家构筑的想象世界之后,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一个个被渲染得神乎其技的科技发明。张卫中指出:“中国作家往往是先通过词语了解某种科技产品和相关知识,这种知识传播方式也决定了很多作家是依托词语建构自己的科幻世界。”[8]晚清科幻小说事实上也确实更多的是在科技新名词的基础上展开的关于“物”的想象。西方科技文明的大量传入客观上为中国科幻文学的诞生创造了技术层面的条件,但这种被动接受之下产生的科技文明却是有先天缺陷的。由于小说家自身的知识体系构成以传统儒家思想居多,对西方传入的科学技术又缺乏理性全面的认识,晚清科幻小说虽然具备了科幻文学关心未来的幻想性特质,但其科学基础却并不牢固,科学技术在小说中经常处于一种“装饰性”位置,对想象之“物”功能的无限制渲染反而成了小说家下意识的集体选择。郭颖颐指出:“唯科学主义从由科学原则推出的文化设定中兴起这一事实,使它成为一种自发的精神现象,经常被现代文明的崇拜者无意识地宣传。”[9]晚清科幻小说中的这种对想象之“物”功能的无限制渲染,正是将科学力量无限上纲上线,进而导致科学理念大于科学内容的唯科学主义思维模式的典型体现,也就是朱军在论述近代科学叙事特征时所指出的“与其说科学叙事已完整把握了光、气、电、力、星、以太的要义,不如说它迅速陷入了一种新的名教崇拜”[10]。
因此,与其用科学技术想象来概括晚清科幻小说的主要特征,不如说晚清科幻小说是建构在对西方科学技术一知半解的小说家对“物”的功能化想象基础之上的。在晚清科幻小说的想象书写中,“物”与“功能”是一种简单直接的一一对应关系。由承载小说家科技改变现实梦想的想象之“物”,再到由各种超出现实范畴的“物”共同构成的想象空间,晚清科幻小说家的创作意图以附着于功能先行的“物”的形式呈现出来。依靠这种关于“物”的想象,晚清科幻小说家以宣传科学知识的名义建立了一个富有“功能主义神话”特色的幻想世界。
二、科技救国主题的反复言说
晚清科幻小说家对“物”进行功能化想象的核心目的是在对想象之“物”强大功能的描摹中反复强调其科技救国的政治文化意图。宋明炜指出:“自科幻进入中国之始,这个文类已被归化,在前所未有的新颖想象之下,流动的是‘中国复兴’的宏伟情结。”[11]晚清科幻小说对“物”的功能化想象所表现出的天马行空和无拘无束,某种意义上正好凸显其科学启蒙、科技救国诉求的强烈性。具体而言,晚清科幻小说家对“物”功能的无限制夸大是为了强调科学发明拥有能够改善未来世界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国家民族命运的力量。这种将科学技术当作改变社会面貌和国家命运的万金油的特殊想象方式,正好是小说家迫切渴望改变社会现状的政治文化诉求的突出映照。
以《电世界》为例,小说讲述了电学大王黄震球自宣统一百零二年开始开办电厂,并用电学的一系列发明在两百年内建造了一个天下无敌的大同帝国的故事。黄震球在江苏省扬州府东境发现一块陨石,用电力加热的方式从陨石中提炼出了拥有磁力的“磁精”。在此基础上,他又将电器炉的温度提高到一万三千度,从中提取出拥有自然发电能力的金属原质“鍟”,只要将“鍟”放在空气中“略略摩擦一番,那空中电气,便如江汉朝宗一般,源源而来,滔滔不竭”[12]。凭借这一只要接触空气就可以发电的神奇金属,黄震球不仅发明了一对不到三小时就可以环绕赤道一周的飞行“电翅”,还制作出威力强大无比的“电气枪”,烧毁了侵略中国的一千支西威国的飞行舰队,之后又飞到西方将西威国的都城烧得片甲不留。除了可以发电的“鍟”外,黄震球还在印度恒河旁边发现了一座盛产金属“鈤”的“鈤质矿山”,并用二十几斤“鈤”制作了三万几千盏“鈤质灯”。“鈤”又叫“电锭”,是一种能够自动发热的金属,因而拥有可以改变气候的神奇能力。黄震球不仅用“鈤质灯”使西伯利亚、南极、北极等地方变寒为暖,还用自己发明的“电犁”“电气肥料”在世界各地发展农业。使用“电气肥料”之后,禾本植物长势和产量都十分惊人,每一穗的米粒产量高达一升,而且全球统一都是一年三熟。鸡鸭猪羊也因为食料富足而养得格外硕大,金华的白毛猪甚至长得像印度的驯象一样。除“电翅”“电气枪”“鈤质灯”“电犁”“电气肥料”外,电学大王的发明还有“电筒发音机”“电光教育书”“电车”“扫地电机”“洒水电机”“电气分析镜”“电椅”等。这些以“电学”为基础衍生出来的想象之“物”显示了电王黄震球对未来世界军事、交通、教育、医疗、农业,甚至自然气候和人的生命长短等方面强大的改造能力。“科幻是一种新形态的景观化的群体性活动,各种奇异的景观是其标志”[13],《电世界》所展示的这些奇异景观虽然都是建立在电王黄震球对“电学”创新发明的基础上,但却远远超越了日常经验的范畴,走向对“物”无限制的功能化想象。《电世界》暗含的这种人力改造自然、中国战胜世界的叙述逻辑在晚清科幻小说中屡见不鲜,《月球殖民地小说》中的“月球世界”、《新石头记》中的“文明境界”、《乌托邦游记》中的“乌托邦”、《女娲石》中的“天香院”、《痴人说梦记》“仙人岛”等一系列建立在对“物”的功能化想象基础上的虚构空间都具有政治稳定、人民富足等近乎雷同的特征。而这些想象也就代表了小说家借助对“物”的功能化想象宣传科技救国理念的朴素愿望。
借用居伊·德波(Guy Debord)“景观”的概念来分析晚清科幻小说中“物”的功能化想象,便能够清楚看到小说家借助想象之“物”为读者勾勒一幅人民富足、科技昌明的美好视觉图景的努力。德波认为“景观是将人类权力流放到彼世的一个技术实现;它是人的内心已经完成的一个分离”[14]。晚清科幻小说家所热衷的停留在对“物”的想象层面的空间书写模式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简单粗暴的景观展示。小说家在对想象之“物”功能的不断展示和描绘中完成了理想空间与现实世界的区隔。“区隔是意义活动必不可少的前提”[15],是科幻小说产生陌生化美学效果的必要条件,而科技便是那个引发一系列变化并能够引导人们走向美好未来的现实技术力量。通过向“读者”(既包括文本外的读者,也包括像《电世界》中的说书人“我”和《新石头记》中的贾宝玉这样以游历或参观者身份进入幻想空间的文本中的人物)展示这些借科学之名想象出来的神奇之“物”,科幻小说家在“看”与“被看”的二元逻辑中建构了自己想要传递的一套科学启蒙话语,振兴国家民族的强烈意识形态也通过这种技术发明展览的方式和盘托出。因此,晚清科幻小说中那个由功能化的想象之“物”组成的理想空间始终与小说家表达科技救国的政治文化意图密不可分。
总而言之,晚清科幻小说家对“物”进行功能化想象的核心目的在于证明科学技术拥有摆脱国家贫弱的现实局面,甚至使中华民族雄踞于世界中心的强大力量。吴岩将这种表现强国梦想的书写方式总结为“愿望模式”,也就是“将以往早就存在了的群体或个体的愿望通过某种所谓的产品或技术呈现在作品之中”[16];方晓庆也认为“晚清文人少有人经历过专业的科学训练,过分强调启蒙的急进心态驱使下,科学小说如同一个被撑大变形的口袋,扭曲着呈现在读者面前”[17]。吴岩和方晓庆的总结都看到了晚清科幻小说的科幻想象存在科学性薄弱而现实功利性较强的弊端,中国强于世界各国的政治梦想被不同小说家重复描述就是扭曲和变形的集中体现,而想象之“物”则是强国幻梦在文本中的具体支撑点。这种将救国梦想寄托于对科技之“物”的功能化想象是晚清科幻小说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
三、现实关切情结的强烈凸显
陈舒劼认为:“无论科幻想象的对象是否已然超出人类的理性认知能力,如果必须叙述,就只能转入人类经验的表达渠道,也就是说,只能叙述可被叙述之物。”[18]因此,无论想象多么离奇怪诞,晚清科幻小说始终具有关注人的生存环境,思考技术与人的关系的现实关切特征。关于这一点,“科幻现实主义”与晚清科幻小说家试图借助科幻手法表现黑暗社会现实的创作特征具有一定程度的契合性。这一理念认为虚拟世界憧憬的各种愿景,或令人大跌眼镜的种种乱象,必然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倒影。任冬梅指出:“科幻现实主义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对现实的再现与批判。”[19]按照她的观点来分析晚清小说家对“物”进行的功能化想象,不难看出林林总总的奇异幻想的出发点往往都是强烈的现实关切情结。除上文提及的科技救国政治文化意图外,在思考如何用科技改变现实的动力驱使下,晚清科幻小说家还普遍选择了以镜像写实的表现方式来隐喻社会现实。他们参照西方列强欺凌中国的方式构筑了未来中国领先于世界的美好想象。在这种线性的思维模式中,想象之“物”不仅是他们描绘美好蓝图的物质前提,同时也成为他们以未来某一个时间点为参照系重新认识社会现实的立论基础。在反向写实过程中他们努力将头脑中的强国幻梦移植到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之中,科技制造出来的理想国越是绚烂美好,反向映照出的社会现实就越是丑陋不堪。通过这样的表现手法,晚清科幻小说中“物”的功能化想象同样也具有冲击力极强的现实主义文学特质。
在晚清科幻小说对众多科技“物”进行的功能化想象中,改造国民身体和灵魂的神奇医学手段可谓最具有现实意义。谭光辉认为:“中国现代作家把中国看作一个有病的躯体,把自己放在医生的位置,为其诊断和治疗,腐烂的身体和腐烂的文明一起构成了整个中国现代的历史。”[20]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医生治病这一过程本身便经常被作家赋予以新知识启蒙旧社会的文化隐喻功能,晚清科幻小说同样也是如此。晚清科幻小说中关于更换脏腑或心脑描写的小说结论几乎相同,即中国人的器官已经被八股和名利侵蚀,已经无可救药,需要清洗或重新更换。海天独啸子在小说《女娲石》中描绘了洗脑院中遭受科举考试荼毒的脑筋的状态,“若将那副脑筋,解剖出来,其臭如粪,其腐如泥,灰黑斑点,酷类蜂巢”[21]。同样,《介绍良医》中的医学博士用狼心、马肝、犬肺、虎胆治好了“我”的病,“人面兽心”的“我”反而开始后悔自己之前只知道吃喝嫖赌的行为,开始有了羞耻之心。同样由于科学知识接受水平的局限,“剖心挖肺”这样匪夷所思的医学描写缺乏基本医学原理的支撑,读者能看到的往往只有滴了之后伤口便可痊愈的神奇药水,以及医生对患者症状一针见血的分析。事实上,小说情节是否符合医学原理也不是小说家关心的问题,借助对医学器物的功能化想象实现改造国民身体、灵魂的愿望才是晚清科幻小说描绘“医心换脑”情节的唯一目的。贾立元认为晚清科幻小说中出现的洗心、洗脑、催眠等一系列带有滑稽戏谑意味的幻想背后事实上隐伏着小说家对“格致/科学”的崇敬,这种崇敬虽然只是在旧有的寓言故事中添加了科学话语,甚至经常是对当时科技新闻的直接搬运,但如果“没有科学提供的基本陈述,国民改造的议题本就无从说起”[22]。因此,医心换脑情节虽然是从现实世界的各种医疗技术出发,但小说的最终落脚点却是以幻想方式疗愈国民精神层面的沉疴痼疾,突出地显示了功能化想象背后所隐藏的强烈现实关怀。
余泽梅从科幻小说所具备的认知功能出发思考科幻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她认为“认知使得科幻文本理性地解释想象的世界,阐释科幻世界与我们自己的经验世界的联系与断裂”[23]。作为一种话语形态的科幻小说不仅以其陌生化的艺术手法强化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也为我们理解甚至预见未来的社会形态提供了一种感性直观的思维范式。因此,从科幻与现实关系的视角研究晚清科幻小说对“物”进行的功能化想象,不仅能够从感性直观的层面看到他们所憧憬的未来世界的具体形态,更能够透过他们所言说的想象之“物”种种不可思议的功能,看到他们渴望借助科技力量改造国民性的强烈现实关切。
四、结语
晚清科幻小说中“物”的功能化想象尽管因为小说家片面夸大想象之“物”的性能、反复强调科技救国主题而导致小说存在整体审美价值不高的弊病,也因为过分指涉作家的现实关切情结而无法避免“开口便见喉咙,又安能动人”[24]的粗浅感,但他们以科幻形式构想未来世界的努力仍有其不可或缺的文化研究价值。一方面,这批处在新旧文化融合阶段的知识分子感受到时代变迁带来的巨大心灵冲击,他们借助科幻想象未来世界的朴素愿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对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重新看待科幻这一文类所具备的认识论功能来说,同样意义非凡。另一方面,正如刘慈欣所说,“科幻不应是一块冰冷的石头……而应是一支火炬,在寒夜的远方给人以希望”[25],通过对晚清科幻小说中“物”的功能化想象的解读,可以看到晚清小说家幻想愿望背后强烈的现实诉求。无论晚清科幻小说中“物”的功能化想象在今天看起来如何荒诞可笑,它们都映衬了小说家拥抱西方科技文明、憧憬美好未来、探索异域空间的最初渴望,是那个特殊时代文化的缩影。如今,类似《电世界》中描绘的改善交通、制造人工降雨、改造沙漠等美好愿景已经成为现实,而那些还没有实现的部分,仍需我们运用科技力量,以敢于突破未知的精神气魄去积极探索。
通信作者:王辉,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1] 达克·苏恩文 . 科幻小说变形记 [M]. 丁素萍等,译 .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 让·鲍德里亚 . 物体系 [M]. 林志明,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3] 陈平原 . 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 [J]. 中国文化,1996(1):114-131.
[4] 包天笑 . 钏影楼回忆录 [M]. 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
[5] 包天笑 . 空中战争未来记 [M]// 于润琦 . 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6] 荒江钓叟 . 月球殖民地小说 [M]// 章培衡,王继权 . 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痴人说梦记等 .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7] 碧荷馆主人 . 新纪元 [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8] 张卫中 . 新词语与清末民初作家的科幻想象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6(6):103-109.
[9] 郭颖颐 .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M]. 雷颐,译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0] 朱军 .“爱先生”与“赛先生”:近现代科学言说的形上之维 [J]. 文学评论,2020(2):153-161.
[11] 宋明炜 . 新世纪科幻小说:中国科幻的新浪潮 [M]// 陈思和,王德威 . 文学·2013 春夏卷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12] 高阳氏不才子 . 电世界 [M]// 李广益 . 中国科幻文学大系·晚清卷·创作三集 .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
[13] 严锋,蒋原伦,孙玮,等 . 新媒介语境下的科幻景观与科幻文化 [J]. 探索与争鸣,2019(8):37-66,197.
[14] 居伊·德波 . 景观社会 [M]. 张新木,译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15] 赵毅衡 . 论区隔:意义活动的前提 [J]. 西北大学学报,2015(2):54-60.
[16] 吴岩 . 论中国科幻小说中的想象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12):17-29.
[17] 方晓庆 . 晚清科学小说:急进的启蒙 [J]. 科学文化与评论,2011(2):90-103.
[18] 陈舒劼 .“长老的二向箔”与马克思的“幽灵”——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社会形态想象 [J]. 文艺研究,2019(10):77-87.
[19] 任冬梅 . 从科幻现实主义解读《北京折叠》[J]. 南方文坛,2016(6):46-49.
[20] 谭光辉 . 症状的症状:疾病隐喻与中国现代小说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1] 海天独啸子 . 女娲石·乙卷 [M]. 上海:东亚编辑局,1905.
[22] 贾立元 . 人形智能机:晚清小说中的身心改造幻想及其知识来源 [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1):88-106.
[23] 余泽梅 . 陌生化与认知: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的科幻小说 [J]. 江西社会科学,2012(1):122-125.
[24] 公奴 . 金陵卖书记 [M]// 陈平原,夏晓虹 .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25] 刘慈欣 . 天国之路——科幻和理想社会 [M]// 刘慈欣 . 刘慈欣谈科幻 .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排版:张馨木 编辑:齐钰 审定:邹贞)
本文链接:https://www.bjjcc.cn/kepu/34575.html,文章来源:科普之家,作者: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版权归作者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