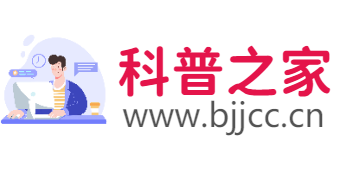《舱外》期刊第一期 我已不再爱人类
时间:2023-01-10 01:45:20 来源:科普之家 作者:高校科幻 栏目:科幻 阅读:147
如果说,疾病带给了我什么,那必然是对死亡漫无止境的恐惧。
131岁,我整整体验了一百年迈向死亡的路程,每一次医学进步都把死神朝远处推去。我拥有的太多,他们也不容我轻易死去。
在身体里数量庞大名目繁复的疾病里,我最先想到的是糖尿病,是其余诸多疾病的根源是我漫长煎熬的发端。在一百年前,我确诊糖尿病的那个年代,还没有人工胰岛可以完全代替身体器官,无数像我一样可怜的人先是吃着名为盐酸二甲双胍的白色大粒药丸,而后等胰岛功能完全失去之后,在肚皮上打上无数个针眼,苟延残喘。
但那时我还年轻,有用不完的精力,有说不完的话,有推不掉的应酬,有不得不吃的饭。而这样的慢性病也让我掉以轻心,以为我拥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不会失去。
它却是最容易治愈的。在人工胰岛问世的那年,我率先体验了不用打针的生活,它的效能全然让我以为自己是个正常人。可那时的我已经不能再做任何的剧烈运动,稍微跑跑跳跳死神就会握住捏紧我的心脏,或是摁住我的胸腔,我看着我的孙子在花园里蹦蹦跳跳,说不清的羡慕。
那些急性的,能当场让我去西天的病反而没有勾起多少我的回忆,急性肾衰竭、突发性心肌缺血、脑溢血,对我来说不过是急救装置的一次警报罢了,往往眼前一黑,再反应过来时已经躺在病床上,除了刚刚缝合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我根本无从得知发生过什么。
我是如何被剥得精光?我是如何被切开身体?我是如何换上了不属于我的人造器官?
无从得知。
在我醒来的时候,身旁总会有一个带着哀戚表情的人。在我三十一岁那年,站在病床旁的是我的母亲,那时的她还很年轻,丝丝缕缕的白发只从鬓角延伸而出,如果她染发染得勤快一些,连这些细微的痕迹也不会有。我还能想起她哀戚的表情,颤抖着的嘴唇不断说着一些今天已经完全想不起来的话语,好像糖尿病比癌症还要恐怖致命,亦或许是因为那时候我才三十一岁,想象中的人生起码还有五十年要饱受这慢性病的折磨才能抵挡彼岸。
我愚蠢的母亲呀,何止五十年,我有足足一百年享受这场折磨。
我的第三任妻子是个贤淑的人,至少与那个时代的年轻女孩相比,堪称典范。我们因医院相识相知,她了解我身上数十种疾病的日常养护方法,在心理诊疗上也有独到的见解。很快这样的日夜相伴促成了我们的婚姻,但我想是没有促成我们的爱情。那时候婚内工作薪资已经入法,她每个月可以从我身上赚取巨额的养护、诊疗费用,而我也可以享用她青春的肉体。每当我想到手指抚过她柔嫩肌肤的触感时,指尖的酥麻就会唤醒沉睡已久的欲望。我后来再搂住她温热的身体,时常会忘记爱情与孤独的界限。起码,在我付给她工资的时候,我不爱她。
我的长子生前是个相当懦弱的人,每当我瞪他的时候就会畏缩着不敢和我对视,这就会让我加倍愤怒——为我生下了这样窝囊的儿子愤怒,也为我的愤怒而愤怒。比起他,我还有更多需要担心的事情,身体、事业、家族,我必须为更多的事情奋斗,活下去成了心头的执念,也是这座医疗帝国的发源。所以我把他丢给了我的第一任妻子,那个安静沉默没有声音的女人。
我确实爱她,在我的青年时代。没什么比一个安静的女人更加令人舒心,在我的同辈深陷桃色纠纷时,我已经一马当先爬山了医疗世界最高的那座山峰。登山的喜悦要远胜于一切物欲,摘取那颗尖峰上的明珠更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那时,全国超过八成的医疗机构掌控在我们家族的手中,全世界最尖端的医疗专家为我服务,我甚至可以站在帝国大厦的顶层,宣称我是世界之王,我是众生命运的主宰者,我能治好几乎一切疾病,也能让所有的医疗机构对你关上大门。
就在那时,我的长子溺毙于浴缸,我的发妻死于食物中毒。他们不加掩饰的向我展现恶意,向我展示:除了杀死我,还有无数种办法让我痛苦。
我的家族替我作出了决定。我的第二任妻子来自于一个历史悠久的金融财阀,她家族的权势力量不下于我们,她是一种和平的象征,象征我们之间达成了和解。我想愿意达成和解的,不包括我。
她是个风流的女人,体态婀娜眼波含情。他们那样的老牌富豪本身就经过了原始的基因筛选,再加上一些后天的医疗技术与化妆品,完全可以作为女星出道。一堆叫不上名字的新亲戚们热络的拉拢我和我的家族,试图用他们腐化堕落的习惯腐蚀像我们这样的“暴发户”。她自然也是个中能手,我甚至怀疑她并非真正来自这个家族,而是他们培养的间谍。
就在那一段日子里,我的次子诞下了后代,也就是我现在床边的那个老态龙钟的男人。这一次,我将他送离了我的身边,交托给我最信任管家抚养。和那个女人本也应当生下一儿半女,但很快我就迎来了第一次严重的肾衰竭。
对于我来说,寻找一个肾脏是相当容易的事情。我奋斗至今,也正是为了我生命的延续。但这份过人的意志力却成了致命的毒药,换进身体里的肾脏接二连三的发生排异反应,不断腐蚀我的身体与精神。最终在我的指引之下,一批有着医学精神与探索精神的小伙子们,开始探索人工肾脏之路,而我就成为了他们最好的试验品。
第十八次手术的时候,我肚皮上的皮肤就不得不被更换为纳米人造肌;第三十五次手术的时候,整整高烧了十日;到了第五十八次手术的时候,我的肚皮已经可以根据要求自动打开与闭合。
但人工肾脏的自主适配和长期使用的完成,是在扩大实验范围之后达成的。
为了让更多和我一样因终末期肾病而濒临死亡的患者有一线生机,我邀请他们免费移植人工肾脏,通过大量的活体实验与长期观察研究,他们终于突破了排异的大门,不仅是肾脏,他们甚至突破到了所有人工器官的大门。
自适配肾脏,可以根据人体的关键神经元模拟原生电信号,除了能完成原有器官的功能外,还可以通过付费完成更多的功能,例如说增强清除代谢功能、增加肾素、前列腺素等产物分泌,不仅在医学上,甚至在生物学上改变了人类。
但这只是个开端。在我治好了肾脏后,肝硬化又找上了我。强大的肾脏极大地增加了我的精力,本已经开始衰老的身体似乎被唤醒了,我像是回到了二十出头,甚至没有糖尿病的年纪。再一度踏上征程的我,拖着已经衰老的身体奔走在各个场合,联合诸多新生力量,组成了恒越世界的商业帝国,不再局限于医疗,万物联网、机器医生、改造人技术都在开阔人类想象力的疆界,我确信我和我的盟友们正踏在走向未来的道路上。
这孱弱的身体再一次拖累了我,肝硬化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我早年间对身体机能的浪费与无穷尽的物欲造就,首先是重度的脂肪肝,这在我因为排异反应食不下咽的日子里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但与终末期肾病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我的团队充满了经验与信心,自适配器官绝不仅限于肾脏,它的终点将是彻底消灭一切脏器带来的负担。
当那颗银白色的肝被我握在手心里时,冰冷的触感几乎要让我落下泪。我知道,我们终有一天会克服这些疾病,迈过百岁的寿数门槛,但这一天来得太早、太突然,肾脏的成功建基于广大的实验体,自适配肝脏却来自于我们最杰出的现代医学家们的勠力同心。我能做的,就是为这些杰出的后继者提供第一例活体实验,即使那时我的夫人还试图劝阻我,但我早就受够了这接连不断的折磨,无论前方是成功亦或是失败,我都要做前往未来的先锋。
很幸运的是,我成功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能在此处喃喃自语的原因,我们又迈过一个门槛,这个肝脏的机能还很原始,仅仅是原本肝脏的替代品。但没过多久,我们就推出了肝PRO和肝PRO MAX。作为PROMAX版本的首个用户,我在那些不离不弃的盟友面前饮下了桶装的高烈度白酒,脸色都不曾有丝毫变化。
这让我的盟友们也心动了,即使他们的身体比我健康的多,有的人甚至有瑜伽教练执照,还有的人清晨四点多就起床锻炼,但他们是和我一样渴求未来的人,谁又能拒绝未来呢?
很快,执掌社交媒体帝国的执行官成为了第一个使用自适配肾脏与肝脏替代原生肾脏的人,在他完成手术的那天,他躺在病床上对我说“把我的智脑拿来,谢谢”。
他就是我的活体广告。开设在各大购物中心的器官更换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建起,抢到预约号的人转手就可以卖出数万美元,我不得不增加数个供应商分享技术来扩大产能。一些狂热者甚至希望卖掉自己的肾脏用以更换自适配肾脏,但肾早已经不再值钱。
也正是在那个时刻,我感受到时机已然成熟,加密货币数字经济已经迈向了虚拟实境阶段,现实资产不断贬值,人们只需要比棺材大不了多少的空间加一个厕所就可以生活,无人机自动化餐饮、虚拟体验装置(这当然少不了神经科学的支持)解决了绝大多数的现实矛盾。我和我的盟友们将手中的剑指向了旧世界最后的顽固敌人——金融财阀们。
我已经老了,却又年轻的让我感到恐惧。一方面肾脏与肝脏的力量永无止息的灼烧着我的意志,唤醒我的复仇欲望,也试图唤醒我的血肉。另一方面,我已经年逾七旬,即使有最好的医疗团队,但高血压、痛风石、帕金森那些老人病仍然在折磨我已经逐渐瘦弱的身躯。
我想,机械最终更胜一筹。我抛弃了我的第二任妻子,撕毁了那段虚伪的和平,向这些不事生产只用手段玩弄着市场的敌人发起最终决战。就在我和她离婚的那天,同盟中的数家公司股价暴跌,数家受他们控制的私募基金开始对同盟中的公司进行做空或是收购,大量或真或假的消息充斥着市场,大量股民在潮流之中恐慌性抛售。
我们自然不会毫无准备,同一时间宣布以加密货币为联盟唯一接受货币,并设立新的以加密货币为唯一准入货币的证券交易市场,地点位于开曼群岛,不受任何国家影响。
漫长的拉锯战开始了,我的许多盟友死在了财阀的暗杀之下,但他们的儿孙接起了权杖,仍然站在我的身边。各国的领导人起初对这个联盟警惕而又防备,但在我们替他们击溃了操持本国财政的财阀家族后,那些狡猾的政治家们很快成为了我的新盟友。
我的自适配内脏有了除心脏以外的内容,它们也在不断迭代之中获得发展,肝1、肝2、肝3,肝4开始,它不再是金属的,而是与真实肝完全一致的外形与材质,唯有内部的电子元件不同,它甚至可以被移植进婴儿的身体之中,并与婴儿一起成长,最终成为一个健康而强大的肝脏,几个试点实验也获得了极大成功,他们在长大后显著比未更换肝4的孩子要来的强壮健康。如果客户有需求,我们还可以配置特殊的防腐蚀涂层,这样在做彩超的时候就会看见五颜六色的内脏。
摩根士丹利在我们的面前倒下、帝国银行向我们屈服、大东京银行以解体的方式苟延残喘,这些曾经数百年雄踞世界的霸主彻底倒下,长达十数年的金融战争让这些财阀屈服,我逼迫他们出卖当时谋杀我妻女的家族信息,这些家族中其中就有我第二任妻子所在的家族。
在马尔代夫的某片天空,我盛情邀请他们参加没有降落伞的跳伞活动,如果侥幸活下来,那游弋的大白鲨们也不会放过这些新鲜可口的食物。那个曾经风情万种的女人抱住我的枯朽的大腿,她的年华也早已不再,衰老已经让她失去了一切。我很想放过她,因为她和我一样饱受衰老的折磨,但当我抚上她的面庞,她眼神里一瞬间的厌恶与惊惧还是让我改了主意。至少今生今世,我不想再看见这张强忍着厌恶的谄媚笑脸。
她落下去前的声音足以让我回味许久,一开始是恐惧,但看着前面一个接一个跳下去,死亡一步接一步逼近她时,这份恐惧就化为了愤怒。她用尽全力撕咬挣脱,不加掩饰的谩骂诅咒,到了最后却又化作了软弱的哀求。
我一直沉默的看着这一切,听她不堪入耳的咒骂,只在她哀求时我才朝她一笑,“在地狱里等我吧。”
她听完,无声的闭上眼,落下的过程中没有发出一丝一毫的声音。
那天的天气很好,海风爽快,我们没有等太阳落下,就飞离了海域。
那时我已经够老了,老到思维都开始迟滞,曾经能够握紧手术刀的手如今连一个装满水的杯子都拿不住。那些疾病痊愈了却在我的身体里留下它们的烙印,时间也亦步亦趋补上几刀。但我的复仇已经完成了,一切爱与恨的人都随风而去,我穷尽一生构建了无比庞大的商业帝国,历史会代替我的子孙后代记住我,我真的可以登上帝国大厦,大声宣布我是世界之王而不被人当作疯子。
我的盟友有的死在了金融战争之中,也有的死在了无情的时光里。一位年轻人刚刚继承了他父亲的位置,向我诉说他不幸早死的妻子。他声泪俱下,仿佛他刚刚得到的一切都是过眼云烟。我看了那个女人的照片,一个曾经以风流而闻名的交际花,但在他口中却是一个只是逢场作戏的女人,她一生只爱过他一人。
我无悲也无喜地看着他,像是在看一个傻子。但我很快由此得到了启发,决定帮助这个年轻人复活他的亡妻。这个计划异常顺利,感谢土葬保留了她的全副尸骸,经由克隆技术近乎一比一还原了她妻子的样貌。一位对此感兴趣的虚拟现实技术大亨提供了剩下部分的帮助——构建一个与她真实生活环境一模一样的世界,并在她的意识世界中快进。为此,大量的情报人员被派出,调查并构建了她完整的生平,起码那个年轻人认为是完整的。
141天后,完成二十三年记忆的她醒来,一眼就认出了他。我们携手撒下弥天大谎,告诉她是这个男人用尽全力救回了她,看着他们热情拥吻,我和那位虚拟现实技术大亨相视一笑,意识到了这个技术的全新用法。
如果说,我的心中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我早逝的第一任妻子和我的长子。这是我剩下的时光里,唯一感兴趣的事情。
又是一年过去了,他们俩成功从虚拟实境中醒来。我又用了一次那个谎言——我将他们冷冻,并最终救活了他们。三个人相拥而泣,只是她似乎不太能接受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将死的老头,并且还娶了另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
我曾经以为他们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后爱我的人,因为我和那个愚蠢的年轻人一样,自以为不为人知的修改了许多记忆上的细节,创造了我理想中的她与我的儿子。
显然,还不够理想。
这让我试图从另一个方向努力,那些女人们曾经用过的伎俩。这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我的腹部本就已经是纳米涂层皮肤,现在不过是把全身都换成纳米涂层罢了。真正的难点在于血管和流淌于其中的血液,造血干细胞的衰老是真正不可逆的,于是我采用了和脏器一样的思路,用替换来取代逆转,大量的纳米机器人涌进了我的身体,在长达半个月的适应期后,站在镜子面前的人又是那个二三十岁的我了。
当我再一次站在她的面前,高兴地对她说“我是不是和以前一模一样”时。她摇了摇头,有些哀戚的看着我,“不,你的眼睛老了,你的眼睛浑浊的容不下我。”
我改造了我的视网膜,将昏花的老眼取代,现在我的眼睛比雄鹰更明亮。
我再一次站在她的面前,高兴地对她说“我是不是和以前一模一样”时。她摇了摇头,有些哀戚的看着我,“不,你的心老了,你的心脏再也不会为我跳动了。”
我迈向了脏器的最后一个难关,现在,一颗真正雄健用力的心脏复活了。
我再一次站在她的面前,高兴地对她说“我是不是和以前一模一样”时。她摇了摇头,有些哀戚的看着我,“不,你已经不再是你了。”
这让我陷入了百余年来最深的困惑之中,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却不知道究竟什么才是自己。我乘着月色走到庭院之中,缓步靠近了她的卧房。本想在睡前与她道一个晚安,却发现屋子里她与我的长子相拥而泣。
我的庄园对他们来说变成了囚牢,我变成了一个心理变态的神经病,我甚至在他们心中变成了一个不知是否还谈得上人类的人,殊不知他们自己才是纯粹的人造人。到了夜尽天明的时分,晨曦的微光划破了阴霾,机械构成的眼睛让我能够直视美丽的朝阳,可最终除了一片白光我什么也看不清。
我呼唤了机器人管家却没有叫佣人,又让机器人管家叫醒他俩,看着他俩惶惑不安的眼神,长叹一声。
“你们走吧,你们自由了。”
后来,我再度听闻他们俩的消息,已经是数月之后了。我的一位长于情报工作的朋友告诉了我这个消息,他们俩最终死于印度尼西亚,被当地武装分子猎杀。而雇佣他们的,正是我的第三任妻子。
她无辜又谄媚的笑笑,继续为我按摩脖子。我没有再说什么,她为我诞下了二儿一女,连怀孕哺乳期间都在努力为我工作,我还能怪她些什么呢?痴痴地望向太阳升起的地方,思维的迟滞让我越来越不想思考,无休止的精力从这具身体中涌现,但我的大脑却再也负担不起了。
所以人之将死,这个白白的房间就会成为一种归宿,无论你的账目上有多少个零,你的帝国又横跨多少个国家,最终为你准备的只是这样一间洁白的房间。
他们,我曾经的盟友与他们的后嗣、我的亲族、我两任妻子的亲族、我的众多后代,洋洋三四百人身着黑色西装围绕在这小小的维生机前。他们的表情或悲伤、或窃喜、或好奇、或连一点表情都做不出来。他们好像一群要参加葬礼的人、好像一群待食的秃鹫、好像一群没见过人彘的猎奇者,好像...
我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列几个好像了。
旁边那张小小的病床上躺着一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和我唯一的区别就是拥有一个不会再萎缩的金属大脑除此之外的部件都是与我身上一致,或者它们的再升级版。当我确认时,医生就会将我现在的大脑内所有的信息拷贝进那个金属脑袋,而我也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永生者”。
“没事的,手术马上就会好的,已经测试过很多次了。”
我冷冷地看了她一眼,让她的笑容凝固在脸上。
我拥有的太多,他们不容我轻易死去,如今,我终于要迎接死神的到来,或是永远的推开死神。
“开始吧。”我说完这句话,意识就开始随着麻醉剂的注入渐渐堕入黑暗。
我反复回想这漫长一生。
可我始终想不起来究竟在这一百三十一年的哪一刻。
我已不再爱人类。
评委评语:
柯昊纯:独白型的自传式科幻小说,讲述了一位医药巨头对疾病、衰老和死亡的斗争,以及期间的发生的爱恨情仇。其中的许多情节单拿出来都可以改编为一整部小说,但最令我感动的还是主角“复活”发妻后,一次又一次地改造自己,只希望成为她眼中理想的丈夫,却离这一理想越来越远。克隆人在自然人的豪宅中相拥而泣,真的是非常触动读者的点,让我们思考克隆人和自然人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是不是有些克隆人比自然人更担得起“人”这个名字。这一个场景就比同一主题的《Mutter》全文更引人入胜,只可惜具体的场景描写和故事细节在整篇文章中占比不高。很期待这篇文章扩充细节后成为中篇。
作者简介:
寒枭,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高校科幻平台编委,福建青年作家研修班学员、闽江学院山鹰文学社副主编,福建师范大学长风文学社主编。
本文链接:https://www.bjjcc.cn/kepu/62189.html,文章来源:科普之家,作者:高校科幻,版权归作者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