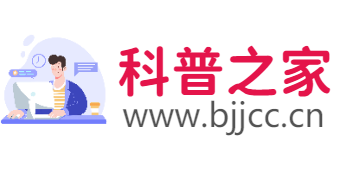敬畏自然 万物共生:论王晋康科幻小说《十字》中的生态思想
时间:2023-02-09 01:45:15 来源:科普之家 作者: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栏目:科幻 阅读:178
王晋康的科幻小说《十字》在2009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2015年改名为《四级恐慌》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再次出版。作品主要讲述了“十字”组织成员梅茵为激发人类的全面免疫能力,将天花病毒从俄罗斯带至中国,对其进行减毒处理后投放到人群中的故事。梅茵虽因此获罪,但她投放的减毒病毒却成功激活了多数感染者的免疫系统,而且,出狱后的梅茵还利用减毒病毒避免了一场原应发生在日本的病毒恐怖袭击。与王晋康的新人类系列(《豹人》《癌人》《海豚人》等)以及“活着”三部曲(《逃出母宇宙》《天父地母》《宇宙晶卵》)等作品比起来,《十字》并不出众,在豆瓣网甚至被一些读者认为是“炒冷饭”和“注水”作品。但笔者认为,该作品虽有不足之处,但却集中体现了王晋康在现代科技飞速发展过程中的生态思考。王晋康将自己的生态思考融入作品中,借助作品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表达自己的生态思想,如“敬畏自然”“生物平等”等。本文拟从“十字”含义的解读、共生思想、善恶观念等几个方面讨论《十字》中的生态思想,并分析该作品在新冠病毒肆虐背景下的现实意义。
一、“十字”:“上帝医学”与“人类医学”
关于标题中“十字”的含义,作者在作品中借梅茵之口给出了解释:“十字是很多原始民族通用的一种文化符号,其本来意义是对自然的敬畏。”[1]197也正因如此,狄克森创立了“十字”组织,每个成员胸口都佩戴着一枚十字架,十字架上刻着“敬畏自然”的格言。这一解释固然呼应了作品的生态思想主题,但仅作如此解读,未免失之浅显。
就一般意义而言,“十字”在现代社会中有着两个方面的指涉:其一为基督教信仰的标识,当然这一标识是由十字架的刑具演变而来;其二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标识。这两个方面的指涉已经成为任何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读者都会具备的基本常识。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2]他认为在认识某一事物之前,认识主体内部已经存在有理解认识对象的“先行结构”。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吸收了海德格尔的这一观点,并将“先行结构”理解为“前见”,认为每一个人的理解都必须受到传统和前见的制约,我们不可能凭空地理解和判断事物,必须以前人传授给我们的知识为前提。在此意义上,“十字”作为基督教信仰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标识就构成了阅读《十字》的“先行结构”或“前见”。因此,读者在阅读《十字》时即使了解了“十字”所含有的“敬畏自然”的意义,仍然无法将之与上述两方面的指涉完全隔绝开来。笔者认为,这正是“十字”作为该部作品标题的深意所在。
“十字”组织虽然不是宗教组织,但却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组织的创立者狄克森在非洲观看角马群大迁徙时给梅茵讲“上帝的医学”——自然淘汰,却受到了梅茵的启迪,并由此开悟。狄克森在金合欢树下盘腿而坐,仰望天穹,整整思考了一夜,创造了“十字”组织的“教义”。在醒来的梅茵眼中,狄克森“目光闪闪发亮”,“脸上焕发着奇异的光彩”,“这一夜相当于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的49天,夜睹明星,开悟成佛”[1]223。作为“十字”组织的创始人,狄克森的死也同样带有宗教色彩。狄克森在审判梅茵的法庭上离世,他当时的形象是“形容枯槁,脊背挺直,银发银须,像一个宗教先知”[1]222。狄克森就这样“坐化”了,如圆寂的得道高僧一般。可以看出,作者为狄克森的悟道和死亡都赋予了一层神圣的宗教色彩,只不过“十字”组织所信奉的“上帝”并不是神,而是大自然。大自然这一“上帝”,运用自然淘汰之医学,淘汰掉“容易患病的个体”,留下“抵抗力强的个体”,进而保证生物世界的“最稳定的平衡态”。
狄克森是一个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流行病学家,供职于美国亚特兰大的亚特兰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经常赴世界各地开展医疗救助,还曾先后两次深入非洲疫区救助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其工作内容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内容有诸多相同之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内容包括应对气候变化与冲突、提供教育机会、保护妇女儿童、保护平民和避难者等众多方面,但提供医疗救助是其主要工作内容之一。梅茵同样怀有一颗医者仁心,小小年纪就和义父一起赶赴非洲埃博拉疫区展开医疗救助,即使后来成为“十字”组织骨干成员并继任教父,也没有放弃对人类个体的关注。梅茵致力于低毒病原体的野外放养研究,就是为了激活更多人类个体的免疫能力。在得知日本受到病毒恐怖袭击后也积极协助应对,并亲自押“毒”赴日,体现了其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狄克森、梅茵及其他“十字”组织成员救助个体的行为,是属于“人类的医学”。“人类的医学”“建基于对个体命运的关切之上”,“与人道主义密不可分”。
在狄克森看来,“上帝的医学”关心群体的繁衍,使生物世界“达到最稳定的平衡态”,但站在人类的立场来看,“上帝的医学”对弱者的舍弃未免过于残忍;而“人类的医学”虽然保护个体,但人类医学的飞速发展使人类自我膨胀,藐视上帝,开始破坏自然原有的平衡状态。经过一夜的思考,“十字”组织的“教义”在狄克森头脑中基本成型,即人类“在变革大自然时要保持一颗敬畏之心,要尽力维持原来的平衡态,学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1]242。作品以“十字”命名,是将“上帝的医学”与“人类的医学”融合在一起,提醒人类要像敬畏上帝一样敬畏自然,要在维护自然平衡的前提下发展人类的医学,救助人类的个体,这才是“十字”的真义所在。
二、共生: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整体主义
王晋康在《十字》中还传达了一种万物共生的生态思想。作者在《十字》第一章借梅茵与斯捷布什金的对话抛出了一个问题:人类有无权利擅自判决哪个物种是敌对物种,并褫夺它们在自然界生存的权利?后面又在第四章借律师杜纯明之口予以回答:“地球生物圈中所有生物都是合法成员,具有生存权利。不能以人类的好恶肆意宣判某个物种的死罪……人类在用科学这个利器来变革自然的同时,也应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不要过于粗暴地干涉……”[1]218这种万物平等和谐共生的观点既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同时又未落入生态中心主义的窠臼,是典型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体现。
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善恶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3]。生态整体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对立。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只有人类才是目的,一切非人类存在物都不过是为人类利益服务的手段[4]178。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主张人为自然立法。生态整体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也不相同,生态中心主义将其他生物放在和人类同等重要甚至比人类更高的地位,主张为了其他生物的利益甚至可以牺牲人类,这一思想否定了人的实践能力,将其他生物置于中心,把人类置于边缘,与人类中心主义一样存在二元对立的思想。生态整体主义则主要强调消解中心和二元对立,提倡主体间性,重视整体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强调多样生物的和谐共存。
作品中狄克森和梅茵都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了生态整体主义。两人赴非洲原计划是旅行,但在接到需立即赶赴埃博拉疫区展开救助的任务时,狄克森并未犹豫;梅茵受狄克森影响怀有一个成为流行病学家的梦想,主动要求跟随狄克森前往疫区,毫不畏惧,此时二人秉承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为了更好地救助病毒感染者,他们希望能够研制出有效药物抵御病毒,甚至杀死病毒,因为消灭病毒可以让人类更加健康,这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体现。不过这时狄克森已经注意到了大自然的神秘和科学的局限性:“自视甚高的科学精英们其实远不能把握科学的副作用。科学家能透过表面,看透较深层面的大自然运行机理,也许还能看透第三层、第四层……但自然界还有第五层、第一百层、第一万层机理呢。”[1]237同时,他还认识到错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狄克森在金合欢树下“悟道”后认识到,科学的迅速发展使人类自我膨胀、藐视上帝,为人类征服自然、随意剥夺其他生物的生存权推波助澜,“科学所引发的灾难和它对人类的造福几乎一样多”。但狄克森并未走向另一个极端——生态中心主义,而是主张沿着进化之路继续走下去,但在变革大自然时要保持敬畏之心,与自然和谐相处。
梅茵接受“十字”组织的教义原本也是“出于人类的利己天性”。她认为,在进化了40亿年的生物圈中最大的受益者是人类,因此人类只有尽力维护生物圈的稳定才符合人类的最大利益。在推行“十字”组织教义的过程中,她的思想越来越趋向于生态整体主义。在法庭审判时梅茵回答记者拉斯卡萨斯说:“经过40亿年残酷的试错过程,能存活到今天的任何生物,都是生命的强者,是大自然不可复制的瑰宝。它们共同组成了地球生物圈,都有在生物圈中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人类只不过是生物圈中的一员,而且是一个晚来者,有什么权利宣布某种生命的死刑?”[1]197梅茵在这里强调了自然界中各种生物都处于平等的位置,哪个物种也没有得到“上帝”的尚方宝剑来宣判其他物种的死刑。梅茵的观点是对人与自然相互对立的二元论的消解,体现了生物之间相互平等、互为主体的主体间性思想。但作为人类的一员,梅茵当然要考虑人类的利益,因此才有对天花病毒进行减毒处理的措施,在保障病毒生存权的同时,尽量减少对人类个体的伤害,这一行为的结果既保障了病毒的生存,又最大程度地维护了人类的利益,是一种双赢的局面,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体现。
三、投毒:“天使之善”与“魔鬼之恶”
作品中“善”与“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面看来,梅茵、狄克森等人代表着“善”,而齐亚·巴兹等人则代表着“恶”。但奇特的是,无论是“善”的一方还是“恶”的一方都在从事着相同的事情——投放病毒。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何为善,何为恶,如何判断善恶?
善是指一切符合道德目的、道德终极标准的伦理行为,也即增进社会、他人和自己以及动植物等非人类存在物利益的伦理行为;恶是指一切违背道德目的、道德终极标准的伦理行为,也即减少社会、他人和自己以及动植物等非人类存在物利益的伦理行为[4]271。因此,判断善与恶的标准主要看其行为结果是“利他与利己”还是“害他与害己”。判断善恶还涉及“道德共同体”的概念,道德共同体是指应该被道德地对待或应该得到道德关怀的对象的总和,简言之就是道德关心的实际的范围。道德共同体也是具有互惠关系的利益共同体[4]149。人类中心主义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为了满足人的利益而随意破坏自然,自然界的许多生物未被纳入人类的道德共同体之中,即使一些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也只是将部分与人类关系亲密的动物纳入道德关心的范围。生态整体主义则将自然视为一个整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具有主观能动性,有责任与其他生物和谐相处,以维护自然的平衡状态。因此生态整体主义主张将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纳入人类的道德共同体,将之视为需要道德关心的对象,病毒亦然。人类和病毒同属一个道德共同体,一方面,病毒一旦进入人体,就有了“长久”存活的保证,人若死去,人体内的病毒也会随之慢慢死去;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病毒,人类固然可以存活,但其免疫能力将越来越弱,生命会经常面临威胁。
在将本应销毁的天花病毒交给梅茵之前,斯捷布什金内心有过一番思想斗争:“对教父履约践言,他不敢确认自己行的是天使之善还是魔鬼之恶。”[1]5他认为,放出病毒虽然可以激活人类的免疫能力,从人类整体的命运来说是“善”,但弄不好会有几十万甚至上千万的人因感染病毒而死,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却是“恶”。反观狄克森与梅茵,他们似乎并未在这一颇有可能成为事实的预见面前退缩。作为作品的主人公,梅茵身上所代表的“善”是作者重点表现的对象。梅茵为了践行“十字”组织的教义奉献了自己的身体、爱情和一生的时间,甚至不惜在牢狱之中度日,她是完全无私的。但她的行为却并非完全利他。从生态整体主义来看,梅茵的行为既有利于人类免疫能力的提高和种族的延续,也保证了病毒的存在,是一种完全的“无私利他”,是一种高尚的“善”。但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梅茵认为,为了高尚的目的,可以用一点不大高尚的手段[1]235,因此她“色诱”斯捷布什金并导致其自杀,“欺瞒”了孙景栓、薛愈、金明诚等她身边亲近的人,导致了小雪的毁容和马医生的死亡,也致使自己身陷牢狱。她的行为是完全的“害他害己”,是一种“恶”。可以说,梅茵是“善”与“恶”并存的。但作者充分肯定了梅茵的“善”,并通过让她进行减毒疫苗研究、拯救千万日本感染者的性命,以“善”行来抵消“恶”,甚至以一生孤独的命运和身陷牢狱的经历对其“恶”实施了相应的惩罚。可以看出,在作者笔下,梅茵是天使,她的“善”是“天使之善”,她的“恶”也是“天使之恶”。
齐亚·巴兹所代表的“恶”是“魔鬼之恶”,是作者着力批判的对象,但作者并未将之当作完全的“恶”。美国的发家史是印第安人的血泪史,美国目前的繁荣与进步建立在一些民族和国家的痛苦之上。痛恨于美国的“罪行”,齐亚·巴兹内心仇恨的种子疯狂生长,致使他最终走上了恐怖袭击的罪恶之路。在齐亚·巴兹的思想中,美国、日本等众多国家的人都是“他者”,被他排除在自己的道德共同体之外,成为他要处罚的对象。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齐亚·巴兹的行为导致了许多人的死亡,他自己也因被通缉而东躲西藏,这是一种“害他害己”的行为,是一种“恶”。但从生态整体主义的角度来看,齐亚·巴兹的病毒恐怖袭击却是一种“善”,这一行为的结果使人类对天花病毒产生抗体,也增强了人类整体的免疫能力,这对人类种族的繁衍来说是一种“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梅茵认为:“从长远上说,齐亚·巴兹的这次天花恐怖袭击打破了病毒真空,也算是一件好事。”[1]133在作者笔下,齐亚·巴兹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略带悲剧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是可悲的,“没有亲人,没有亲情,没有快乐,没有幸福”,为了报复,他用全部财力和智力来培育天花病毒,实施的两次恐怖袭击却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尤其是对日本的袭击,半个月过去了,“东京人活得结结实实”,他把心淬得越来越硬,却在一个妓女面前表现出了软弱的一面。他放了莎玛一命,表明他淬硬的心在那一刻也软化了。最终,他把自己变成病毒,打算“以肉弹方式把埃博拉散布到东京”,不过是困兽的最后挣扎而已。
梅茵和齐亚·巴兹,一女一男,一个生于中国长在美国却心怀“万物”,一生为“他”;一个生长在美国却执着于“故土”,一心复仇。显而易见,作者对梅茵和巴兹的态度比较复杂,并非如表面那般爱憎分明,而是将他们当作自然这个“上帝”的一体两面。作者将梅茵和巴兹一个描绘成天使,一个描绘成撒旦,前者的行为是“天使之善”,后者的行为是“魔鬼之恶”;另一方面,作者又将二人当作“上帝”的代言人,既施惠于人类,又惩罚人类,其方式既有和风细雨式的温情,又有疾风暴雨式的残忍。作者如此处理的目的也很明显,就是要提醒人类敬畏自然,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与自然和谐相处,尽力维护自然的平衡状态。
四、结语
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王晋康写了一篇名为《超级病菌》的短文,发表在当年的《科幻世界》第6期。他在文章中认为,自然界进化出人类无法抵御的超级病原体的可能性很小,人类经过漫长的发展已经与环境建立了一种动态平衡,病毒在进化,人类的免疫系统也在进化。王晋康对人类自身的免疫能力充满乐观,但对人类的本性却不太自信,他指出人类还有一个最大的敌人——自己,一旦人类打破了自然界的动态平衡,就有可能使某种病毒对人类造成重大危害。因此,王晋康主张,人类在掌握科学的同时应该保持对自然的敬畏,当不得不打乱自然界原有的平衡时,应尽可能做补救工作。这篇文章体现了王晋康的生态思想,即将自然看作一个处于平衡状态的整体,人类作为自然中的一分子,要尽力维持这种平衡。可以看出,这是王晋康对“非典”疫情的观察和思考,对当时身处疫情之中的人们来说,有着重要的思想参考价值。《十字》出版于2009年,但作品所传达的思想,与这篇文章基本一致。可以说,《超级病菌》和《十字》是“非典”之后的两次警示。
遗憾的是,“非典”之后,病毒大规模暴发的情况并未停止,如非洲的埃博拉,如当下的“新冠”。截至2022年年中,新冠病毒肆虐已两年有余,波及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人数超过了5亿人,累计死亡人数多达600余万。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许多人将目光转向有关病毒灾难的文学或影视作品,如小说《鼠疫》(La Peste)和影片《感染列岛》(『感染列島』)、《传染病》(Contagion)等,试图从中寻求一丝寄托,找到某种启示,或者获得某些经验教训。尤其是《鼠疫》,甚至一度成为畅销书。“非典”时期著名学者周国平就曾重读《鼠疫》,并写了一篇名为《“非典”期间读〈鼠疫〉》的书评。加缪的小说中,鼠疫结束后人们欢欣鼓舞,全城人倾巢出动庆祝噩梦的结束,人们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中,每天辛勤工作,业余时间赌牌、泡咖啡馆和闲聊。这一结局暗合了黑格尔的名言——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周国平也担心“非典”之后我们会像《鼠疫》的结局一样,“生活一切照旧”,因此他希望经历过非典”的人能够从“非典”中得到一些启示,即认识到祸害会以各种形式始终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为了防止它们蔓延,人类必须对现代的生活方式做出改变。对比王晋康的《超级病菌》和周国平的《“非典”期间读〈鼠疫〉》可以发现,两篇文章对“非典”有着相同的思考和期望,都认为病毒(祸害)始终存在,人类必须做出改变。
《十字》中梅茵等人的“投毒”行为虽稍显极端,但书中传达的生态思想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在“非典”之后,世人再次陷入影响范围更广的新冠肺炎疫情,此时阅读或重读《十字》,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感受,也可以从作品中得到更多启示。
通信作者:马俊锋,河北经贸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日文学比较研究、科幻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王晋康 . 十字 [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2] 马丁·海德格尔 . 存在与时间 [M]. 王庆节,陈嘉映,译 .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3] 王诺 . 欧美生态批评 [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4] 王海明 . 新伦理学原理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排版:张馨木 编辑:齐钰 审定:邹贞)
本文链接:https://www.bjjcc.cn/kepu/63307.html,文章来源:科普之家,作者: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版权归作者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