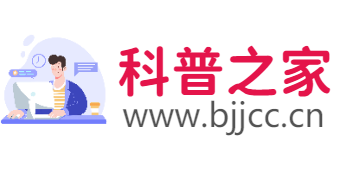金鱼大学(上)
时间:2022-07-06 12:36:53 来源:科普之家 作者:科幻空间 栏目:科幻 阅读:119
《金鱼大学》
作者:杨枫
说来惭愧,我的实验室生涯并不光彩,充满了翘班、争吵和失败的实验。
这和我自己不争气有很大关系,不过,就算没有我,实验室的氛围好不到哪里去。第二次热潮又过去快二十年了,人工智能技术依旧没有本质突破,但是上级文件要求学科设置要综合全面,学院必须保留这个研究方向,结果就是每年都有一群像我一样的倒霉蛋被分配到这个组,跟着教授和屈指可数的前后辈在所谓的“科学前沿”重复着几十年前的工作:网络结构优化、特征工程、半监督学习、准确率竞赛——史称炼丹。
工作压力如山似海,有时,我们甚至一天要在实验室待二十个小时。实验室比宿舍更像家。我们在这里工作,吃饭,休息,搞黄色,甚至还孕育出了我们独特的娱乐方式:调教实验室的生活助手。这活动是我们为数不多的慰藉。就连助手本身是某届师兄师姐为了活跃气氛而编写的作品——戴上AR眼镜,会有猫耳女仆或英伦管家(当然,也可以是定制的形象)出现在你身边,嘘寒问暖,点外卖,热咖啡,在你啃数字文献时贴心地帮你翻页。
没有什么AI不是从智障做起的,我们的也不例外。我的助手——一只爱尔兰小妖精——最初甚至在我们开组会时大爆粗口,原因是那时我们尝试向程序中加入性格要素,语料库里却混入了奇怪的样本。不过,在经年累月的轮番训练以后,助手的服务水平已经有了显著的提升。三字班的学姐们强化了它的自然语言识别能力;后来导师亲自动手,上载了一套增强学习机制;五字班的师兄用脑机接口采集的数据量化了每个人的幸福指数,把它纳入到增强学习模型的奖惩图里;助手的默认虚拟形象则是美院的同学设计的……到我这届时,给助手打升级补丁已经成了一项仪式,不完成它,就算顺利毕业,也会留下不小的遗憾。
很不幸,如我所说,我的实验室生涯并不光彩。我既没能融入学术氛围,也没能产出什么科研成果。入学第二年,我还因为课题不顺而和导师大吵一架,此后连实验室也不去了,有事只管走MR系统远程联络。
一直到开题答辩前的那个学期,我才又主动找上导师,因为开题要求我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一篇论文,而那时的我对此毫无头绪。
不仅如此,我也没想好要给助手做什么升级。
导师虽然气愤,却没刁难我,只是丢给我一篇大师兄写废的论文,让我自己琢磨琢磨。寒假,我一个人留在了学校,翻阅十几GB的参考文献,试图从中发掘灵感,至少也要找到论文中的解决方案的可改良之处。然而大师兄却是个和我一样的废物,废稿写得一塌糊涂,令我全然不知从何下手。和我相比,他唯一的长处大概是脸皮厚,而且勤奋刻苦。延期毕业了一年以后,不仅勉强发了另一个子方向的论文,还在寒假离校前悄无声息地提交了助手的升级补丁。而我却只能一边抓耳挠腮,一边后悔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读研,而不是接下本科毕业时洒向我的各路offer。
抓耳挠腮不能解决问题。腊月快要结束了,眼看着新年临近,我却仍然在原地踏步。一天夜里,负面的情绪搅成一锅粥,令我彻夜难眠。我的工作站这时还宕机了,气得我索性套了两件外套,跑到园子里暴走。要么调理好情绪,要么冻死算了。带着这样的想法,我从北走到南,从东逛到西,最后筋疲力尽,停在了荷塘旁边。
就在这时,我知道了师兄究竟给实验室助手打了什么补丁。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一头实验室在喝水。
它趴在水边的卵石路上,屁股顶着假山,另一侧的墙面露出忧伤的表情,两扇对外开的窗户挤成一团,下方窗框微微翘起成朝上的钝角。换水用的虹吸管一头插在窗边的鱼缸里,另一头穿透冰层,探进池塘深处。鱼缸里的金鱼只剩下了一条,翻在水面,在水流的摆布下摇摇晃晃。
面对这超绝震撼的场面,我一时间停止了思考,过了一会,给大师兄拨去了电话。
接到我的电话,师兄显得有些意外。
“你怎么还在学校?”
“论文还没弄好。你的毕设呢?”
“还在死磕。”
“……”
“……”
开场的寒暄让我们都很尴尬,话题便迅速转进到眼前的景观上去了。
“你的实验室不太高兴。”我把摄像头切向湖面。
“哈哈,被你发现了。”师兄这才露出了得意的神色,“这是一套可视化系统,套用了西门子的数字孪生引擎和腾讯的电子宠物套件,我把这些整合在了一起,然后把之前的幸福指数接在了宠物的情绪模块上,你看到的实验室之所以心情不好,就是因为这个。”
他指了指鱼缸,我这才意识到那条翻白的金鱼其实是我的化身。如今大家都回家了,我的情绪便代表了实验室的情绪。
“它都能做什么?”我问。
“让我想想……常用的语音指令它都听得懂,不如你试试。”
我试着把实验室脑补成家里养的土狗,结果,实验室虽然听得懂我说话,却表现得活像只癞蛤蟆。我让它伸爪,它便把一侧的虚拟光纤和电缆戳进我的手心;我让它叫两声,蓝牙耳机里便传出了门禁刷脸机的确认提示音,同时实验室的正门开始不停开闭;最后,我命令它打滚,它僵硬地翻了个身,却翻不过来了。
“哈哈哈,物理引擎有改进的空间,但还挺可爱的。”看着实验室四仰八叉躺在地上,师兄挠了挠头,“房间的尺度是可变的,没事的时候多遛遛它,让它学习一下姿态控制。”
“明白了。”我两手一收,把实验室缩到课桌大小。
师兄又跟我介绍了数字孪生和情感映射的部分,讲他是如何从表情包般的切尔诺夫脸谱图联想到立体成像上的。
“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条真正的金鱼。我只是找了一条我家里养的品种做了三维建模,然后取了一组体态特征来映射情感要素。打个比方,尾鳍颜色的深浅代表了‘愤怒’,既然金鱼本色是红的,那尾鳍颜色越浅,就表明这种情绪越反常。这样一来,只需要看一眼金鱼,就大致能明白一个人的心情是怎样的……”他滔滔不绝道。
“那看来我现在还挺生气的。”我瞥了一眼金鱼薄红色的尾巴,叹了口气。“行吧,这样释放一下,也多少放松点了。你接着说,我听着。”
于是师兄继续侃侃而谈,我则恢复了体力,接着沿路前行。在科技语言的洗礼下,房间里的金鱼渐渐停止了翻白。实验室也不再愁眉苦脸,筋斗云一样,摇摇晃晃地跟在我后面。虽然我对师兄讲的东西意兴阑珊,但是在心情低落的时候,有人能像这样一直陪我说话,倒也不错——至少能让我暂时忘记烦恼。
沿清华走一圈要很久,途中,道路两旁的成像热点开开闭闭,电源灯荧光闪烁。
走到半程,身处异地的师兄话锋一转,又谈起了未来,说他毕业以后打算去跟朋友创业,现在已经在资金筹备阶段。听他讲商业模式和生态链蓝图讲得热火朝天,我却又陷进了自怨自艾当中,只觉前途一片黑暗,却又不想败了师兄的兴致,只得把金鱼调节成仅对自己可见,同时偶尔心不在焉地应和几句。
走到校医院的时候,师兄的表情忽然变得严肃起来。
“你在改的那篇论文太差了。”他说,“别一棵树吊死,现在换课题还来得及。”
“……可是我没什么好想法。”
“有的时候,其实创意也不完全是翻论文翻出来的,你代码写得很漂亮,说不定能在做项目的时候发现一些东西。”说到这里,他露出懊恼的神色:“嗨,下学期老板打算把实验室和助理打包申请项目基金,之前要不是这套东西是我偷偷摸鱼做的,就也拉你一起了。”
见我不说话,师兄又说:“不如这样,现在这个系统里涉及情绪映射的部分是我原创的,设计的核函数还不够稳定,有的时候还不能准确表现被代理人的心情。你正好在学校,拿你自己做做实验,帮我改一改。老板想让我后面再发篇文章,但我不想再费心优化了,回头你弄完,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就给你了。你看怎么样?”
“……算了别说这个了,天挺冷的,没什么事我先回宿舍了。”
赶在实验室肚子里的水壶嚎叫起来之前,我中断了远程通讯,甚至没有和师兄道别。他后来又拨来了几次,都被我拒绝了。
我赶回宿舍,洗干净被风吹得生疼的脸,回屋倒头便睡。我不喜欢受人施舍,从小到大,一切问题都尽量靠自己解决,连读研资格都是在年级前十里挤破头才争取来的。如今在折腾了这么久的情况下,不管师兄的提议出于何种动机,我都不需要,因为它只是进一步证明了我自己的无能,而这是我绝对无法接受的。
然而,三天之后,我却不得不再次给师兄发消息。向他询问提议是否仍然有效。
走投无路之下,我甚至没有脸面开启视频通话。
“没问题。”
师兄倒是豁达,一反学期结束前的郁闷状态。只是把资料打包发给了我,然后大致和我讲了讲思路,一句也没有提我唐突挂他电话的事。
“我妈叫我去吃饭了,加油,新春快乐。”
“……谢谢师兄,新春快乐。”
当晚,我洗了一个热水澡,和家人吃了一顿云年夜饭以后,久违地睡了个安稳觉。睡前,我又翻了翻论文,接着和妖精打了半小时冒险游戏,然后小小地哭了一会,这下才终于缓解了接受他人施舍产生的强烈罪恶感。
零点,新年夜到了,数字烟花在远方的城区上空无声翻滚。火柴盒尺寸的实验室在床头散发出柔和的米黄色氖光,恢复了活力的金鱼则悬浮在妖精的怀中,悄无声息地吐着泡泡。
总之,时来运转也好,拾人牙慧也罢,师兄给我的新材料终于带来了足够多的启发。我先取得了导师的许可,接着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情绪映射模型的优化当中。我自己的性格还挺感性的,遇到状况,情绪波动很大。这反倒能让我在很大范围内测试模型的效果,我因而得以在爱宠行为观察期间,迅速找到问题,重新进行演算。就这样,在寒假的后半程,我终于逐步化解了纠缠了我一学期的困难。
二月底,休假结束了。学校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鱼缸里的金鱼也跟着多了起来。消息不胫而走,师兄设计的建筑宠物迅速成为了校内师生口耳相传的热门谈资。
到这时,映射算法已经基本上大功告成,因变量曲线上的毛刺已经被我悉数平滑干净,而且也能在标准数据集上取得SOTA[1]了。虽说如此,但是对此时的我来说,比起挑战极限,还是毕业要紧。保险起见,我没有选择那些顶级平台,而是投了一个排名较低,但是过稿率高,回复速度快的A类期刊。交稿那天,我压着截止时间,在网站上提交了文档压缩包。弹出提交成功的窗口后,老板仰头陷进转椅里,带着满脸释然,跟我说“你总算开点窍了”。直到那时,我才终于放下心来,开始着手准备开题答辩。
所有这一切都是师兄的功劳,但是自始至终,我都没有觉察到发生在他身上的异变。上学期,导师骂他骂得很凶。在我帮他写程序改论文期间,我曾经注意过他低落的情绪。不过,他那时跟我说,他正在努力尝试自我疏导。因此,面对他在寒假期间的豁达,我却只是以为他已经找到了足以说服自己继续下去的动力,却没有想到疏导本身也完全有可能导向别的结论,从而创造出完全不同的人物弧光和人生轨迹。
四月初,我的论文擦边通过同行评议。两天后,鱼缸里最大的锦鲤一头撞在玻璃壁上。导师怒发冲冠地打了几通电话,又风风火火地奔向紫荆公寓。电话没有人接,等待他的是空无一人的床位。师兄人间蒸发了。肄业退学不代表人生终了,这便是他的答案。
师兄玩失踪这年,我们的导师刚刚五十八,眼袋臃肿,微微驼背。
人工智能刚热起来那会儿,他开始从事相关研究,也做出过一些尚可的成果,却始终没能成为开山祖师爷级别的人物,再加上中间争夺经费得罪了人,后面又遭遇了行业不景气,到我们这届时,他已经很久都没有亮眼的业绩了,职称也岌岌可危。这次申请课题基金差不多算是他的最后一搏,结果身为主力的师兄却不辞而别,其结果可想而知——在我去办公室的路上,整个走廊里都回荡着他的咆哮。
见导师前,我一直在给师兄打电话,后来又发短信给他,但所有消息都石沉大海。倒头来,我还是不得不顶着导师罗刹般的面孔,默默接受了命运。一口巨大的锅扣在了我的头顶——接手师兄的活,完成接下来的课题申请任务。
“可是我还要准备开题呢。”我说。
“开题不重要,随便糊弄一下就行了,先做这个。实在不行,拉几个本科生来帮你。”
呵,说着轻松。
我内心翻涌出无数黑色辞藻,最后却只是点头默认了导师的安排。于是,到开题答辩以前,我不得不忍受了一整个月的高强度盘剥,同时还要反过来压榨我的后辈。死亡四月来临了,组内成员的情绪几乎都一落千丈,实验室自然也成天横着张臭脸。我们起初还会关照一下它,后来忙得昏天黑地,也没精力去调节各自的心态,便索性放任不管了。
五月中旬,我在开题答辩上挨了一顿臭骂,原因是准备不充分。值得庆幸的是,评委老师还是放我过了。答辩经过有如过山车,我的金鱼的体表也红白翻涌。
开题一周后,组员们总算备齐了必要的课题申请材料。为了说明项目的二期研究价值,我们发布了实验室助手和虚拟宠物的试用版,校内人员可以以办公室为单位申请账号。为了更直观地给基金委的评审员们演示效果,我们还剪辑了一套宣传视频,放在了项目官网上。做实验,调程序,写文档,剪视频,做报告,联系各部门领导……这些平日里并不繁重的活,一和开题答辩撞了档期,就让人严重消化不良。临近开题时,我已经彻底失去了时间观念,连发牢骚的精力都没有了。而就是从这时候起,组员开始越来越依赖生活助手的激励和安抚。实验室几乎变成了熬煮心灵鸡汤的大锅,连我的妖精都开始一本正经地讲起了乔布斯和冯·诺依曼的丰功伟绩,有的时候还要同时扮演柔情闺蜜和知性俊男。当导师终于认可了我们的准备工作时,我们几乎是争先恐后地往宿舍赶,唯恐慢一会,休息时间就又不够了。
虽然万事俱备,但是对这个赶鸭子上架的项目,我却仍然心存疑窦。然而时间却不容我担忧。项目上线之后,我匆匆睡过一觉,醒来后立刻便转去攻略毕业设计了。和很多半年前就已经做完毕设主干内容的同学相比,我已经大幅落后了。
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做了一些数值分析和时空演算,着力于落实已发表的论文里陈述过的未来展望。几天过后,虽然进展并不算快,但一些统计结果却已经让我确立了几个猜想,如果能通过实验证实它们,就可以以此作为出发点,来设计新的情感映射模型了,不出意外的话,新版本的粒度会更加细腻,纳入到实验室系统里,也能改进各个部件的表现。
周末,在妖精的提议下,我打算稍微喘口气,拖实验室出去走走。出门后没多久,导师忽然发来消息,让我看看试运行系统的用户反馈。我打开一看,发现尽是些负面评价,心里顿时咯噔一下,但仔细一看,对方的言辞都比较温和,而且反馈数量也不多,甚至还有像师兄一样想卷铺盖跑路,觉得我们比助手更能回答他的困惑的人。
虽然隐约感到有哪里不正常,但是这时的我全无提议撤回项目的勇气——一有这个想法,我便想起导师那张铁青的脸。考虑到反馈同质化比较明显,也看不出什么规律来,我最终认定问题可能只是因为助手的心理疏导能力还有待提升,便回邮件联系用户,索要更详细的问题描述,打算等反馈再多些时,再研究研究。
就这样,导师的问题被我们一直拖到了六月份。
到了六月初,负面反馈变得更多了,校内也流传起各种各样的传闻。
而就在我终于鼓起勇气去找导师聊的时候,一则新闻却先我一步,引爆了躁动的氛围——隔壁学校的新闻学院联合心理系的研究小组,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里公开了我们学校的校内立体影像。数字沙盘上的增强现实空间里,遍布着实验楼、新老图书馆、体育场、食堂、绿地和一百七十五座公寓楼的数字影像。房屋和房屋挤成一团,个个垂头丧气,致使校内风景有如百鬼夜行。报告的标题是《当代学术社群的可视化心理画像分析:以清华大学为例》,矛头直指校内的高压气氛。
此事一出,学校里立刻炸锅了,上上下下都乌烟瘴气。导师不得不四处调解,在会议室和办公室间奔来跑去,有时还要公开出面向公众解释,却反而将大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他自己卑微的科研履历上去了。而我也不得不再度搁置我的毕业大计,带头重返这个越来越让我感到不耐烦的项目。
我们的关注重点并不是燕大报告所暴露的问题,而是助手能否有效改变这个局面。导师不知道动了什么关系,竟然靠吹牛皮要来了一周的调试期,条件是关闭虚拟实验室的部分,免得继续落人口实,同时助手应当尽快发挥作用,以便帮校方圆场。然而事与愿违,一周后,局面依旧。更令人头大的是,在没有数字宠物陪伴的一周里,我们在七手八脚的同时,还要应对领导、记者和其他同行的轮番轰炸。而我们的用户对那些虚拟房屋的喜爱程度显然比对助手高,因为关掉前者之后,我们收到的抱怨信反倒更多了。
接着,就在我们准备举白旗的时候,更严重的问题爆发了。燕大报告引起的学风大讨论刚刚偃旗息鼓,忽然有一天,物理系的一名博士生申请退学,次日,两个建筑系的学生在紫荆操场大打出手,甚至还动了刀子,而我们实验室的一名外校实习生忽然被同组的女朋友甩了,一时间精神恍惚,最后不得不中止实习,寻求心理辅导。
这些事若是分拆到五六年里,本该稀疏平常,却忽然集中爆发,自然再度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校方本来迫于舆论,公布了一份“减负计划”,却被这突如其来的二次风波搅得鸡犬不宁。院长算是导师的半个同门,这时也终于顶不住压力了,把导师直接交到院长办公室去训话。但是事态却依然越来越糟,不久后,就连教工当中也出现了濒临崩溃的人。原本无人问津的心理治疗室人满为患,就连邮箱和电话都被打爆了。
在所有的案例中,生活助手都没有起到鼓励师的作用。我们虽然都知道助手能力有限,却没想到竟然会差到这个地步。身为项目的主力,我再次陷入了寒假时的焦虑中,做梦都会梦到头顶悬挂着成串成串的利剑。导师传唤我时,我已经回滚到了研二和他吵架时的状态,满脑子都是借口,内心却也清楚,只要不解决眼前的问题,推脱的理由再充分也没有用。
我走进办公室,肩头的金鱼左摇右摆,象征恐惧的头部一片惨白。
屋里坐着一名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导师迎上来,并没有如预期那般发火,只是声音僵硬地问我怎么看待当下的局面。
“我觉得造成极端状况的原因很复杂,在很多案例里,当事人的心理状况很可能已经超出了助手的处理能力。我正在评估这个临界值在哪……”
“但是也有很多例外,”导师打断了我,从桌上拎起一个窗口,推到我面前:“比方说数学系的这例,状态跟你差不多,为什么你就行,他就不行呢?”
我哑口无言。说我心态比那男生好无异于抬杠,而且这种回答毫无意义。如果不能给出有理有据的答复,我们唯一可靠的结论,只有助手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用,之前的成效不过是安慰剂效应而已。
我木然地看着导师,导师眉头紧锁,一言不发。事情已经来到了一个僵局,必须依靠外力,才有希望得到解决。而这也不简单。整个项目已经经历了过多的升级,由于从一开始就没有确切的总体规划,因此代码风格混乱,文档残缺不全,要迅速展开分析,只有把参与其中的人都找到。考虑到很多前辈已经出国深造,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另一条出路则是开源代码,向学术界和产业界寻求帮助。而这样做的代价,便是项目本便有限的科研价值会迅速被全世界的学者、工程师和资本家们瓜分得一干二净。
就在这时,在我和导师中间忽然弹出了一个通话请求。
坐在一旁的年轻人露出了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导师则仰天长叹一声,伸手戳开了来电提醒。
接下来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像做梦一样。
导师把所有人都叫到了办公室,靠着窗台,开始分配任务:“不硬挺了,找外援吧。我看小杨也要顶不住了……小张小陈,你们两个去照着毕业生联络表找人,能找到多少是多少……我这就找上面汇报情况……小杨,你文笔好,晚些时候过来帮我写通讯稿,尽快找门路投出去……”
“哎呦——你麻利点儿好不好啊。”众人散去以后,见我还稀里糊涂,导师急了:“大头都要回来了,也不用你管事了,就把我刚刚说的那几件事弄好就行了,明白没有?”
在导师的责问下,我点了点头。导师这才满意,开始在身边一层层堆砌会议窗口。我回到实验室,在工位上趴了十分钟,然后爬起来梳理大纲。在我离开导师办公室时,拉师兄一起创业的老板也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告辞去接师兄去了。
[1] SOTA,全称为State of the Art,指在特定问题下遵照特定指标所能取得的最优结果。
本文链接:https://www.bjjcc.cn/kepu/33733.html,文章来源:科普之家,作者:科幻空间,版权归作者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