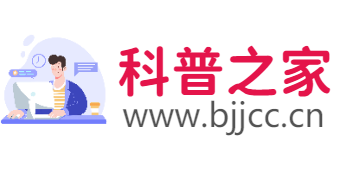金鱼大学(下)
时间:2022-07-06 12:36:53 来源:科普之家 作者:科幻空间 栏目:科幻 阅读:105
两小时后,我写好了初稿,发给导师看。过了一会,导师叫我去大会议室找他。
师兄在场,他的合伙人也在场。半空中还坐着几名我不认识的大人物。导师对我使了个眼色。我在真人和幻影们的注视中,摸到角落里坐下。导师继续向上级汇报,领导们则冷冰冰地听着,点头摇头,偶尔否定一些想法,比如说大规模找外援的计划,但也给出了相应的备用方案,比方说用师兄合伙人那边提供的数据平台来做分析支持。
导师让我写的通讯稿最终变成了一份详细的问题描述和系统使用教程。又一个通宵过后,我们把两份文档、事故数据和项目源码打包发往校方指定的几家单位。群发完成后,我扛不住了,在工位上睡了六个小时,再醒来时,师兄不在,听说是被合伙人拉到公司办事去了。
等回复期间,我靠着八卦和线索,大致拼凑出了导师找回师兄的过程——学期伊始,师兄并没有真的下定决心逃学,不然连新学期注册也不会去做。离校以后,他没有出城,而是轮流借住在几个朋友的家里,躲避着各方的轮番轰炸。事情闹大以后,导师找到了师兄的合伙人,那人二本毕业,虽然不在乎师兄的学历,却在乎他的人品。他知道师兄参与了这个项目,跟他说他再不出面的话,合作创业就不必再提了。师兄这时也意识到躲躲藏藏终究不像话,于是便给导师拨去了电话。
对此,我无话可说。师兄不辞而别后,我始终对他抱有一种复杂的情感。他回来后,这种情感更混乱了,远远超出了金鱼肤色的表达范围。连妖精都时不时和我说:“有的时候,真是搞不懂你。”
师兄再回来时,数据和程序都已经上载好了,各家机构也发来了确认回复。我看得出师兄看我的眼神变得很奇怪,但在这个关头,他也和我一样,在努力克制内心的情绪。
在校园内,保卫处配合海淀区公安机关,加强了治安管理,当天下午,在新玉树食堂接下了一名从楼顶一跃而下的学生。此后,心理辅导站也在附属医院的支持下迅速成立了。
又过了一天,四名前辈远程连线我们,说下班之后可以帮忙看看。多方联合的事故调查工作就此拉开帷幕。
为了方便做数据分析,我们取消了隐私壁垒,把所有的虚拟生物汇总在一起。一时间全校漫天死鱼飞舞,缩放到鸟瞰视图,仿佛发了霉。翻白沉底的鱼横七竖八,一身白斑,鳍条破裂。当时的媒体因此称此事为金鱼池事件。
到了这时,虽然心存诸多不满,但我们都以为既然有了这么多外援,事情的进展应该更顺利才对,便都努力保持克制,谨小慎微地埋头苦干。导师和师兄的矛盾暂时被束之高阁,我也按捺下内心的躁动,尽管一到休息时间,我们便会像仇家一样避开彼此的生活轨迹。
事实证明,这种工作模式非常消磨斗志。每天起来,在前去实验室的路上,我头顶的金鱼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徐徐褪色。而且没过多久,我们便从往来邮件的频率里,觉察到其他机构消极怠工的态度。联合作业因而未能展现出它应有的效率。很快,人们谈论的便不再是哪方会先攻克难题,而是哪方会先失去耐心。
师兄回来以后,明显想要戴罪立功,什么事情都大包大揽,没日没夜地干。而我为了压制心中的怨念,也把自己埋在各种机械化的辅助工作中。有了数据平台的支持,不到一天,事故数据便经过清洗、集成、分类和一系列后续操作,最终以脱敏的形式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把处理过的数据抄送给同行,然后用爬虫汇总他们的分析结论,以浮动信息气泡的形式将关键信息悬浮在实验室的会议桌上空,排列在条形图、折线图、雷达图和关系网络图之间。写爬虫,做报表的工作也由我承担下来——只要沉浸在在这些事情中,我便能暂时忽视内心的烦闷。
先失去耐心的是校方。
在领导的反复催促下,我们几乎每隔半天就要给出一组分析报告。但是上头却依然不满意,一方面,很多行政部门的负责人搞不懂我们在做什么。另一方面,受舆情压迫,他们只关心解决问题还需要多少时间。
不够快。
这都什么东西。
快点。
每次汇报,他们都这样暗示。
于是,上级逼问导师,导师再逼问我们,而我们只能互相试压,然后把积怨转嫁给助手和宠物。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如果把这些领导的心情打包在一起,搭一个虚拟办公大楼,会是怎样一副光景。
这时的实验室已经配备了最好的研究工具。然而,大多数时候,科研并不是工具好就能加速解决问题的。面朝翻滚的数据海洋,却始终发掘不出有意义的规律,这让在座的所有人都万分沮丧。师兄则更为焦躁,如同一名发了疯的魔法师一般,在自己的身边堆满了悬浮在半空的公式和符号。从他的表现来看,他对很多东西的理解都很肤浅。他的极限,大概也只是把已有的程序包组合在一起,让它们能够有效地协同作业罢了,深究一点原理,就一问三不知。结果一遇到难题,还是得我帮他弄,帮他解释。
与此同时,我还要挤时间去赶我的毕业设计,而地球不是绕着我转的,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我大白天犯困的时间越来越长,最后在一个非常不巧的时间点,上眼皮打下眼皮,错过了导师的一句指示。
“杨杨,导师让你把数据下钻一级。”身边的学姐推了推我,我一个激灵,险些大叫出来。
睁开眼时,面前是一群神色僵硬的市区级干部。我手忙脚乱地挥挥手,却险些关掉桌上的立体图,又折腾了几下,才终于调出导师要的东西。
会后,导师直接组会上发作了,指名道姓地批评我,说不能干就别干了。
我盯着他的脸,他也盯着我。
我眼前掠过一扇无色尾鳍,接着视野一片模糊。
“不干就不干,干不干都一样。”
“你说什么?”
我的脸一阵火热。
“我说干不干都一样!一年前也是,现在也是。废物,废物,废物!我当然知道我废物!一年前我就知道了!早知这样,我就不该过来读研!”
我对着导师大吼一气,跑出实验室时,耳边还回荡着嗡嗡蜂鸣。
怒火中烧,我在学校里漫无目的地暴走。最后果不其然,被四处找我的师兄撞上了。
“你要去哪?”师兄在校门口拦住我。
“出学校。”我没好气地说,“哪里都比这里好。”
妖精从胸前的口袋里探出半个身子,点了点头。
听我这样说,师兄又露出了他刚被找回来时的神色。
“别这样。”他说,“导师也是压力很大,这时候还是互相体谅一下吧。”
“互相体谅?”我气笑了,“你把这个项目甩手给我的时候,怎么不体谅我一下呢?”
“我不是把核心的成果也给你了嘛……”师兄显然被我打了个措手不及,再次精准踩雷。
“我不需要!”
围观人群开始把我们包裹在中央,但我已经看不见他们了,眼里只有师兄这个靶标。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是个错误。你知道我后来花了多大的力气,往里加了东西,才终于把我自己的工作填充到和你的一样多吗?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就是为了让我显得不那么可怜!结果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些确立自己的成绩的机会,马上就又要收拾眼前这个烂摊子!”
师兄被我吓到了,哑口无言地愣在原地。
聚集的人群阻塞了校门,保安过来调停,却被我甩开了手。我越说越气,反倒一点也不困了,只管把师兄骂得狗血喷头,把所有的诅咒都喷射到他身上。
“那你想怎么办!”
最后,师兄也受不住了,困兽一般反问我。
我没理他,转身推开人群,走出校门。
先让我静静。
我擦干眼泪,本来想这样说,但是刚走出校门,我却忽然发现妖精背上的实验室变了模样。在我和师兄吵架时,实验室活像《千与千寻》里的腐烂之神,游走在它的腹腔里的金鱼几乎全都在垂死挣扎,但是我出校门以后,它的心情似乎好了些,至少停止了嚎啕大哭。
师兄赶上来,我推开他,又走进学校。
病鱼多了一条,腐烂之神再度泪流不止,眼泪从断裂的管道里奔涌而出。
我又走出校门。鱼儿随之消失,腐烂之神也不再哭泣,只剩愁眉苦脸。
我又试了一遍,现象依然如故。
我捧着实验室,看看师兄,师兄也看看我。
在这之后,我们谁也没说什么,只是一前一后,重新赶往实验楼。一个猜想击穿了我的脑海。我冷静了下来,开始盘算要如何利用数据来论证它。
回到实验室,导师还在气头上。见我又回来了,便要发作。
“等下。”师兄拦住了导师。
“小杨可能有发现了。”
导师这才退后两步,任我展开数据空间。
“我刚刚出学校的时候,实验室的心情似乎变好了一点。”导师冷笑一声,我没理他:“这提醒我了。之前的这些案例,就结果论,有不少都包含一个或者多个人的离校。这就让我联想到我们的增强学习模型的评估指标了。”
“评估指标怎么了?”导师问。
“我们用的是罗曼诺夫-秦算子。”我从大师兄堆砌的一团乱麻的符号里抓出了一把算式,搭建起矩阵和方程式的城堡,把导师和俄国教授共同提出的群体幸福指数呈现在众人面前。“这个算式虽然漂亮,但是计算复杂度很高,所以我记得很多开源实现都采用了近似算法。我怀疑这些近似算法有问题。”
“这块我确实是用开源软件包做的。”师兄挠挠头。
“系统,打开代码编辑器,调取一个案例出来,开Debug模式,在所有调用了RomanovQin这个函数的地方打断点,开单步调试。”我对助手说。
复盘开始,受害者的幸福指数一路下跌,他那个用户组的群体幸福指数也一路下跌。接着,在临界点处,断点处的代码指向了一个简单得过分的算式——
np.mean,平均值。
好吧,真是粗暴。
我关掉断点,和实验室的同僚们一同看完了剩下的复盘。有了这个结果以后,后面的事故分析便只是顺水推舟了。我用几个不等式性质论证了算子和平均值之间的局部近似关系,后来联系上编写开源代码的工程师时,他说他确实也是这么论证的。情绪分布的散点图则表明:清华校内的状况刚好落在了算子的均值等价区域。
而如果我们用平均值来衡量群体幸福感,问题便显而易见了:生活助手如果无法有效提升所有人的幸福感,就会努力剔除幸福感最差的人。而启发了它的,正是大多数校内人士都经常做的事:在压力过大的时候,离开学校,到外面放松一下。
一开始,助手归纳出来的经验还是正常的。但是出去放松的人终归还会回来,回来以后。很多人又会迅速回归原来的状态,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然而,师兄的案例却带来了一种新的启发——也许可以让这些人一去不复返,这样一来,助手就可以长期维系群体幸福指数的稳定。我们又据此做了一次聚类分析,结果是:在退学博士的案例中,博士身边的发条矮人给他灌输了一堆退学创业成功的人物传记,而这正是师兄逃学的出发点。在其他类型的案例里,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在这些“诱导退学案”中,生活助手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算表现得再栩栩如生,它也只是算法的牵线木偶而已。在它的世界里,堆满了盛装着电击器或蜂蜜罐的箱子,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它的每一次行动要么打开宝箱,享受奖励,要么接受处罚,遭受电击。在日常情况下,这再正常不过,但高压氛围下的校园却让它不管如何行动,都只会获得更多的惩罚。于是,一间间教室,一幢幢房屋都在我们的烦恼之下承担着加倍的痛楚。接着,一些人承受不住精神重担,开始用实际行动给助手提供灵感。一开始这不过是偶发事件,却足以改变奖惩图的数值分布。记录下行为模式以后,生活助手便开始照猫画虎,沿着业已发生的悲剧的轨迹,把校园逐步转化成了受社会达尔文主义驱动的黑暗丛林。这是校园的反抗,是二百余只土木宠物的复仇。
听完汇报,导师如释重负,让我们赶紧写一份书面版的给他,他去跟领导讲。等他汇报完,天已经快黑了。他叫我和师兄去办公室,和我们说明天会有一场新闻发布会。
我本以为他又要我们帮他写讲稿。但是这时的导师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一边啃指甲,一边看向窗外,若有所思,活像一尊燃尽了的炉子。
“干得不错,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
我不知道他的鱼现在是什么状态,但是和我的应该差不多。
导师让我们先回去休息。我们点点头,各自回宿舍睡觉。但这一觉并不安稳:虽然发现了问题的成因,但是善后工作还很漫长。
次日风平浪静。我汇总了事故分析期间的细小成果,发现其中有些内容可以搬运到我自己的毕业设计里,忙活到傍晚,导师来电话了,要我过去。
会议室里,众人齐聚一堂。导师总结了之前的工作,又交代了晚上新闻发布会的时间、地点和一些待公布的后续措施。课题凉了,助手全面下线了,取而代之的是数量更多的真人医生。导师没有说等在我们组前方的是什么,但我们都知道,经过这番折腾,这个组肯定保不住它唯一的教授了。对此,我本该感到忐忑不安,毕竟我是组里唯一的应届毕业生。但经历过所有的波折后,如今的我却只是感到一阵空虚,满心想赶快逃回到毕设里。对这时的我来说,比起毕业,做毕设这件事好像变得更重要了。
“晚上新闻发布会,你们来了的话,直接走小路到后台,免得出麻烦。到时候我一个人上去讲。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感谢你们。”
说完,导师对我们深鞠一躬。
人走楼空,实验室里只剩下导师、师兄和我。我们又坐下来,聊了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导师说,他打算提前退休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退不行啊。”他说,“不过,鉴于事态控制得还可以,没有致死案例,所以啊,责任还是尽量我来担。大家都挺不容易的,别耽误了你们这些年轻人。”
听到这里,师兄绷不住了,但导师让他别说话。
“我做科研做了这么久,后面的十几年基本都白费掉了。你跑了以后,我一开始确实快被气死了。但是后来也觉得可以理解。”他看向窗外,属于他的锦鲤在天空上悠然盘旋,“前一阵子,跟外面的那些什么都不懂的人解释我们的东西,虽然挺累,但解释清楚了,能让人家理解我们,其实也很有成就感。”
“所以以后我打算去做做科普,你们知道艾萨克·阿西莫夫吧?或者卡尔·萨根?我觉得,我们这个学科现在虽然处在这个状态,但是从这次的事故来看,其实还是有潜力的,只不过这些潜力都分散在不同的交叉领域。既然现在我自己的路走不通了,那把我走过的路,把我们走过的路讲给更多的人,把这个领域延续下去,也许以后这种潜力就会被后人挖掘出来,就跟当初的深度学习三巨头一样。”
“不过,即便如此,我对你也很失望。”他话锋一转,对师兄说:“失望的地方在于,你远见不够。这个项目进行到现在,你自己的那个非线性优化系统的论文明显能从里面得到很多启发,就算再推迟一个季度毕业,也不至于退学。结果临门一脚,你跑路了。现在又赶上这茬,我也没有脸面去求人再给你机会。且不说这些,你瞧瞧把你学妹折腾成什么样子。”
师兄低下了头,我依然什么也没有说。
“当然了,这确实是一种选择。退学是一种选择,像你学妹这样继续坚持下来也是一种选择,一条路跑到黑也是一种选择,退休搞科普也是一种选择。关键在于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并愿意承担后果。”
“可能这就是失败者的视角吧。”
他少见地点了一根烟,任云雾缭绕一会后,感慨道。
“总之,虽然你在清华的生涯算是完了。但是既然又回来帮忙了,咱们便也不至于恩断义绝,回头有什么需要,我是还尽量帮你。”
“其实,结合事故结果,也应该可以再攒一两篇……算了,就这样吧。走吧,发布会要开始了。”
导师最后说道。
“……以上就是本次事故的完整成因。虽然我们研究小组要为本次事故负大部分责任,但是在此,我要强调一件事,那就是这件事也暴露出师生对自身心态的认识极度肤浅。生活助手只是一个助手,它不应被当成朋友,伴侣或亲属,更不能被当成心理咨询师。有需要时,我们应当去寻求真正有意义的帮助。”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下面山呼海啸的闪光灯,面对外面举牌抗议的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属朋友,导师平静地做完了报告。下台之前,他面对记者们高举的手掌和流媒体存储设备,深鞠一躬。这件事断送了他的科研生涯,但至少,他在最后还是保住了一些尊严。
后来的事大多不值一提。金鱼池危机得到了化解,导师被校方辞退,换上了另一名谢顶教员。我并不是事故的始作俑者,除了换了老板之外,毕设一切照旧。
实验室催生了灾难,却也启发了很多科研方向,让伦理体系建设、智能体测试框架、空间渲染、数据科学等领域都或多或少地前进了一小步。澳洲的一小撮开发者甚至搭建了一个专设论坛,供亲历者讨论切磋。后来,该论坛转型成了一个基金会,甚至还出版了自己的一类期刊。局面看上去欣欣向荣,只是,一段时间内,再也没有哪方敢像我们这样大规模地部署未经长期测试的系统了。
师兄办完了肄业手续,继续去和他的合伙人去混了。他没有再追问我怎么看他,我也没有再提这件事。新闻发布会以后,我们一起吃了顿饭,饭桌上聊了什么,现在已经不记得了。正如导师所说,这是一个失败者的故事,我们都是失败者,没有理由互相指责。更何况再怎么说,师兄毕竟也是帮了我一把的。
半年后,紧赶慢赶之中,我终于做出了我所期待的成果,顺利毕业,毕业后又把毕设包装了一下,发了第二篇论文。在一家社交网络公司面试时,考官看了我的论文和笔试结果以后,说我数学分析能力很好,虽然不适合目标岗位,但他可以把我推荐给一家金融公司。我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名金融码农,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进阶成了操盘手,踏上了追求财务自由的道路。奇妙的是,尽管我以为至此我已经彻底与学术绝缘,但是在当操盘手时,我却又发了几篇统计学习领域的论文,还担任了一场母校办的建模比赛的评委,见到了很多酷似当年的我的学生。
导师揽下了几乎所有的罪责,从而彻底终结了他的科研生涯。针对此事,他写了一本回忆录。书虽然名声不佳,但姑且还算畅销,稿费被他全部捐给了前面提到的那家基金会。
这件事为他挽回了一些声誉,后来,我还听说他又做起了技术顾问的工作。但是六十四岁那年,一名流浪汉持刀袭击了他。事后调查表明,那名流浪汉曾经也是清华的学生。他并不在金鱼池风波的波及范围里,甚至也没有退学,只是幸福指数长期处于低落状态,但他却将自己的烦闷和坎坷的人生归罪在了生活助手的头上。
飞来横祸又把我们这些流落各地的失败者聚在了一起。我们在导师的病房里齐聚一堂,带来了慰问礼品和各自社会故事。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师兄带来的礼物不是别的,正是当年的实验室系统。他虽然已经创业失败,但与合伙人至少算是和平分手,正在另外一家集成商集团那里做海外项目经理。
面对导师,他手捧实验室,身边金鱼环绕,活像一名微微发福的河神。他说当年的经历带给他很多启发,至少教会了他如何做人。因此,他租了云服务,想重新搭建尘封许久的虚拟实验室,作为对那段时间的纪念。
我们都同意了。
复活的实验室不带有任何功能,只是我们当年的心态的回放工具。我偶尔还会把它调出来看看,有时是为了怀旧,有时是为了在宣讲会上为我的自我介绍增添些味道。
但更多的时候,我这样做,只是因为我想看宠物耍宝。当初设计这只蛤蟆小屋的时候,我们都心怀困惑。但是如今,我已经不需要它了,因为我的疑问已经得到了回答。
本文链接:https://www.bjjcc.cn/kepu/33734.html,文章来源:科普之家,作者:科幻空间,版权归作者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